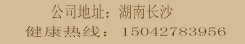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腰包 > 腰包特点 > 她伸手抱起炕上的被子,小梁只好跟着来到东
当前位置: 腰包 > 腰包特点 > 她伸手抱起炕上的被子,小梁只好跟着来到东

![]() 当前位置: 腰包 > 腰包特点 > 她伸手抱起炕上的被子,小梁只好跟着来到东
当前位置: 腰包 > 腰包特点 > 她伸手抱起炕上的被子,小梁只好跟着来到东
文
张瘦石
人冷了,可以找个地方取暖,心冷了,却很难再暖和过来,你冷了一个人,其实是你冷了两颗心。一道菜凉啦,可以拿去再加加热,一颗心凉啦却再很难加热。——题记
一提起马车店,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了解,但是从张家胡同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
马车店相当于今天的旅馆、旅社、宾馆一样,但它又与今天的旅馆、旅社、宾馆有所不同,简单来说,马车店就是牲口与人共同歇脚的地方。
店里住的人大都是外乡客,路上累了一天,人困马乏,晚上找个店住下,洗洗手,烫烫脚,条件好的还可以洗个热水澡。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滚在一起,住的都是大通铺,就是用木板或者砖头在地面上搭建的那种床铺,很少有单人间或者双人房间。当然,也有的大通铺二三十个人紧挨着挤在一起睡。
在店里住宿,外乡客多数吃馒头和咸菜,有时候也有油条加稀饭,鸡蛋是奢侈品,几乎没有,但是卖货人跟外乡客不一样,他们手里有钱,出去吃羊肉包子,驴肉火烧,或者羊肉泡馍,有时也吃小炒肉或者凉拌菜。
“福来顺”,在当地是最大的马车店,院子四周建有围墙,不知道店家是为了进出方便,还是为了节省建筑材料就是没有大门,整个院子只有一个老头守着。
牲口,一般栓在拉脚的马车杠子上,车把式不管外出拉什么,在店里只要停下车,先把麻袋从车上一把拽下来,解开绳子,敞开口,麻袋装着是牲口吃的饲料和干草,供拉脚的马和骡子食用。
水是车把式从“福来顺”井里提上来的,马车店里有一眼水井,井口上设有一架辘轳,车主人顺着麻绳把水桶送入水井,用手轻轻摆动辘轳上的麻绳,然后摇动辘轳把柄,盛满水的桶就会从井里慢慢提上来,供拉脚的骡马饮用。
马车店杂人很多,一般都是拉脚的,走路的,做小买卖的,算卦的,担柴的,赶集的,上店的,南腔的,北调的……各色各样的人都有。
那时候,凉台大平原上和现在的国道边,据说就有不少马车店。
凉台平原,位于潍渠两河流域,属冲积平原。
由于原上常年受季风影响,每年夏季,潮湿闷热,特别是走进暑期,整个凉台平原上像一个巨大蒸笼被暑热所笼罩,风丝不透,热力不减,空气中还弥漫着香蒲、芦苇、水草、泥土里都透着淡淡的清香。
停下脚步,你仔细闻一闻,潍渠的河水里还夹杂着一股浓浓的鱼腥味,又体现出两河流域三角洲那种特有的味道。
原上,水分充足,土地肥沃,盛产一种特殊的植物——水柳。
水柳条是编笸箩、簸箕、箢子等生活器具的上等材料,直至今天,胡同还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南张洛下地屋子——揍货。
说起南张洛揍货,大都是找农闲季节。秋后,男人放下手中的杂活,一个个走进地屋子,按工序分:头遍水,二遍呢,三遍四遍是编织。
头一天晚上,揍货人端起水瓢用力喝一口水,把腮帮子鼓得像喷壶一样,“噗噗”几声,把嘴中的水喷到柳条上,这叫清水润条。然后,把锋利的席刀放在地上,拿昨晚刚刚润过的白柳条,从刀刃中穿过,两脚用力踩住地上的席刀,右手把柳条用力一拉,只听“嗤”一声,那柳条跟布条似的破成厚薄均匀的片状,这叫扒柳条瓤子。
其他人手脚并用,各人编织手中的物件,扎针,穿麻,打底,插条,编织。时辰不大,一个玲珑剔透的箢子在手中完成,这就叫下地屋子——揍货。
接下去是织边,封口,上把子,最后一道工序是熏白,找一间小屋,四周堵得严严实实,把编制好的箢子、簸萁、笸箩等放入室内,在搪瓷碗里点燃硫磺,把门关好,待三天之后取出,这就是胶东半岛和鲁中山区生活中的箢子、笸箩、簸萁等生活用品。笸箩又分针线笸箩、干粮笸箩,烟灰笸箩,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艺术品。当然,箢子又分为:一升、二升、三升和半箢子,笸箩、簸萁则分大小不同。
“老伙计,你在傻想啥哩?”回头一看,不知啥时候老梁已站在身后。
老梁是胡同里唯一的上门女婿,在我们乡下,当地人也称其为倒插门,听说他以前用小车推着箢子、簸萁、笸箩……外出赶集卖货,晚上住宿多数睡马车店。
我朝他笑了笑,解释道:“想小时候揍货的场面哩。”
“那有啥好想的,不就是下地屋子揍货吗?”
说着,他抓起地上的暖瓶,从圆桌上拿过一个茶杯,咚咚倒满一杯热水,右手端起来,贴近自己的嘴唇却没喝,又赶紧放下“你的文章我看过哩”。他抬头看我一眼,“年龄大啦,眼也跟着花,我是带着老花眼镜看完的”。
他分明是想说,前些日子《青海湖》发表的散文《戏童》,里边有一些描写张家胡同里的事情,
“怎么样?”
“不错,挺好的,但是没有把卖货人的真实故事和欺诈手段写出来。”
“咋,当初你们赶集卖货还有猫腻?”
“当然,这叫隔行如隔山”。
这时,他脸上又显出一种得意洋洋和莫名其妙的神秘感。
通过跟他闲聊,我才真正了解到卖货这一行,以及卖货人欺诈手段和入行中的猫腻。在过去,一个人想干卖货这行当,你得先入行,也就是平常说的拜师,你得勤快,你得龙睛虎眼,你得请客送礼……否则,你一辈子入不了这行当,入不了行,你的货物就不好卖,甚至卖不出去。当然,你也挣不到钱,最后被伙计们明里暗里用各种手段把你挤死哩。
“怎么才能入行?”我不解地问。
“你说我?”
他睁大眼睛看着我,辩解道:“我是拿两斤烧肉,两瓶景芝老白干换来的。”说到这里他用手指了指自己,“在入行之前就得对把头有所表示。”
“你说的把头就是指群里的头吗?”
“是的。”他肯定地回答。
我冲他点点头。
他看我想继续听下去,又进一步向我解释:“把头就是行规里的头人,一般来说年龄比较大,威望比较高,说话好使,好用,能让人家服你,当然口碑也好,只有这种人才能有资格做把头。”说完,他嘴角又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意。
“哎!你就送这么点东西?”我笑了笑“也太少了吧。”
“这还少?在队里干一天活才挣三毛钱,马车店住一晚上才五毛钱。”他怕我不相信就睁大眼睛,向我继续解释,并且显得十分认真,“那时候,买一斤烧肉七毛钱,一瓶白干一块三毛钱,玉米两毛钱一斤,麦子三毛钱一斤,我送的礼不少啦。”
我笑了笑,又问:“哦,你算是正式入行啦”
“那里的?这才算是刚入门槛。每天晚上,在店里你得打热水给把头洗脚,烫脚,擦脚,端水。早晨起来,你得给他端饭,伺候他吃饭。路上,你得推货物比较重的车。在分钱的时候,你分得也比他们少。”
“没有举行正规的入行仪式?”
“没有,但是入了行,你得行拜把仪式。”
“拜把仪式繁琐吗?”
“不不,其实很简单,跪下磕个头,就算是弟兄,有福同享,有难同受,以后弟兄们之间互相照顾。”接着,他又补充“我拜把头作为干爹,入了行以后好得到照顾,说起来你小时候可能还对他有印象,就是你们第三生产队里的人,姓王的。”
听他这么一说,我还真有那么点印象。
早前,听说过卖货这一行是有行规的,也听别人提起过跟着把头卖货的故事。
据说,为了垄断市场,那时候都是把头自己定价,挣的钱除一少部分给卖货多的人外,剩余的大部分钱伙计们平分,也就是说伙计们共同把货价抬高,即使你今天没有把货卖出去也照样分钱。
大集体那会儿,一个三升箢子卖到三十元,回家到生产队报账才十块钱,大部分钱落入卖货人的腰包。伙家们拜了把子,相互统一了口径,外界人根本不知道这些内幕,只有内部人才知晓。可想而知,那时候的卖货人都肥得流油。
“其他人不眼红吗?”
“怎么不眼红?”
他冲我嘿嘿一笑,“后来,队长找他的亲戚跟着一起去卖货,把头就采取一日代劳的手段,拖垮他,累死他,垄断市场围堵他,后来那亲戚实在没法干了,自然而然再也不跟着卖货了。”
“慢点,你说一日代劳拖垮他,累死他是啥意思?”
嘿嘿,他又憨厚地笑了笑,“也就说,头一天下午上好货,晚上启程,当天晚上就赶出一百多里路……待天明时,已赶到安丘辉渠、沂水一带,跟货的人脚上磨出血泡,不敢走路,吃的也差,自然而然就退出卖货这一行当。过后,队里用跟货这种办法行不通,又采取加价的方式,每个箢子由原来的十元加五元,我们卖货人又不干哩,编出来的货物卖不出去,到最后还得启用我们这些人。”
听到这里,我突然冒昧地插上一句,“那时候夜店里有姑娘吗?”
“你是说路边店里那些陪睡的大嫚?”
“是的。”我点点头。
“没有,没有。”他晃着脑袋跟拨浪鼓似的,摆着手,尽力辩解道:“那时候风气真好,马车店里没有小姐,也不敢有。那些年讲究作风问题,男女双方同意也不行,检举出来就会游街,就会批斗,就会低头认罪,还得在大会上检讨。谁敢?就是有那个贼心也没有那个贼胆哩。”
“我才不相信哩。自古至今,只要人存在,男女之间就有交往,只要有交往就有扯不断理还乱的私情,就有千丝万缕藕断丝连的那种情感。你想想,那时候你们有钱,小伙子长得也帅,一出门就是半月二十日,身边不可能没有女人。”
我说话的语气很重,“你说没有?谁相信!”
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自语道:“你说的也对,那个年代我们有钱。”
我紧盯着他“钱,这个东西,一旦离开人就是一张废纸。”
听到这里,他抬起头往远处看一会儿,又低下头叹一口气,“唉,那个时候,也许我把钱看得过重,否则,回来再多给她一点。”
“男人不要把钱看得过重,把钱看得过重会失去人味。”这时,我又强调“好男人是讲究感情的,特别是我们凉台平原上的汉子,但是男人离开钱那是废物一个。”
他轻轻点了点头,嘟囔道:“一个男人整天在外,身边没有一个女人,那也是枉然。”
我听话里有话,接着诱导他“你说得也是大实话,不是所有的心事都可以说出来,有些事只能自己懂,有些话只能说给自己听。”
我见他低头沉默不语,可能是刚才的话已触到他的痛处,于是又接着说:“人冷了,可以找个地方取暖。心冷了,却很难再暖和过来。你冷了一个人,其实是你冷了两颗心。一道菜凉啦,我可以拿去加加热,一颗心凉啦却很难加热。男人长得再帅,担不起责任照样是废物一个。”
最后一句我说的比较严厉。
这时,他眼圈红红的似乎噙着泪,嘴上却断断续续的辩解,“这件事在我心里藏有四十多年了,我从没对外人说过,也不愿意对别人提起,现在想想我真对不起她,也没有尽到一个男人的责任。”
哦,原来老梁年轻的时候外边有个女人,那个时候不兴叫情人,而是称相好的或者暖被窝的。胡同里的人背后戏称搿伙,热炕头的,主事的,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方言,但是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老婆以外的女人。
老梁在年轻的时候,结识的那个女人名叫凤玉,是安丘辉渠人。
那年冬天,凉台平原上特别冷。
当年还是帅小伙子的老梁,一同跟随卖货人去西山里赶集。傍晚,卖货车队刚过了辉渠,他推的小车就嘎吱嘎吱叫唤,开始还认为车上货物太多,又沉又重,被冬天的大风刮的箢子或者笸箩响,可是小推车越走越沉,越走车越响,尽管他用力还是追不上前面卖货的车队,渐渐地,他就落到车队的后边。
到后来,小车直接推不动了,他才停下钻到车底一看,傻眼啦,小推车挤铛了,那嘎吱嘎吱地响声是钢珠相互摩擦发出的声音。
天渐渐暗下来,卖货的小车队顺着弯弯的山路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
西北风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一个劲地嗖嗖刮个不停,那声音又像一个喝醉酒的流浪汉,跌跌撞撞,打着呼哨,四处乱窜,偶尔,寒风还夹杂着秫秫粒大小的雪霜子,直往脖子里钻。唉,这“鬼天气”,这讨厌的西北风。
小梁把手放在嘴唇上,使劲呵了一口,热气一团一团的,随即飘向身后。他缩了缩脖子,又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衣领,尽量把头和脖子缩进衣领里,以此抵挡外来的寒风,围着小车来来回回直跺脚。
他搓着手,又气又急,一个人在半道上正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头脑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唉!有啦,不如今晚上先进村住下,歇歇脚,待明天上午,借工具把车子修好再走。对,就这样办。想到这里,他走进村敲开村西紧靠路边的一户人家,给他敞门是一位小媳妇,虽然天黑看不清她的脸面,但听声音也就三十上下的年纪。
小梁上前对她说明来意。
女主人开始有点犹豫,后经他再三解释,说住一晚上明天就走,并付给她比马车店里再贵一倍的价钱……在他的哀求下,女主人最后答应了,但是必须住进院子的西小屋。
小梁急忙点头表示谢意。女主人待客也很热情,不仅帮他把小车死推硬拉拽到院子里,还要去烧热水给他烫烫脚。
小梁急忙上前拦住,并再三推辞,女主人只好作罢。
这是一户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院子西边是两间低矮的小草屋,里面储藏一些日常杂物。正北方是三间正房,比小西屋高出许多,正房分东屋和西屋,也是主人和家属的卧室。中间是伙房,那个时候叫当门或者叫灶房。
西小草屋偏房,属阴,夜里冷得厉害,又加上屋内没有取暖设备,睡觉的板子床也通风透气,小梁盖着一条被子,在床上翻来覆去冻得难以入眠。
女主人很贤惠,也很善良。
一个外乡客来到家里借宿,车上还装有货物。她有点不放心就披上外衣来到院子里,查看一遍觉得没事就往回走,刚走近小西屋窗下,听见小梁在西屋里翻身弄得板子床咯吱咯吱响。这么晚了他还没有睡?偏房属阴,冷得厉害。想到这里,她轻轻推开门,
“这位大哥,你若不嫌弃,就搬到北屋住西间住吧!”
不知道西小屋太冷,还是女主人的话太热情,小梁感激地朝她点点头,抱起被子跟着女主人来到北屋西间。
北屋属正房,白天朝阳。
炕,虽然没有生火但不透气,炕西头紧贴屋山还有一个储藏地瓜的窖子。看得出,女主人平时怕冻坏地瓜,白天在炕上生过一次火,伸手一摸,炕席底下还隐隐约约的余温。
她点燃蜡烛走进西间,借着微弱的烛光,这才看清眼前这位女主人,她生的眉清目秀,端庄大方,可能是今天遇见生人的缘故,咋看上去,羞中透涩,涩中带柔,在羞与涩之间还透着善良和贤惠,豁达与开朗,温柔与果敢。在那不长不短的睫毛中间,还镶嵌着一对黑宝石似的眼睛,聪明富有灵气。每当她说话时,那睫毛伴随着眼神有节奏地上下闪动,给人感觉到朴实,厚道,干练,诚实……她很好说话但留有分寸,每当说话时面带微笑,嘴角上还常常挂着一丝甜甜的笑意。看上去,女主人也就三十挂零的年纪。
她帮着把被褥铺好,才回头莞尔一笑,端起正在拼命燃烧的蜡烛,消失在今天这个美丽的夜色,连同那个美丽的倩影。
夜半时分,西北风又像疯婆子似的,在院子里来回晃着大叶杨的树梢,一阵嘶喊,一阵嚎叫,一阵阵树枝吱嘎吱嘎撞击声,大风掀的屋外窗户档子也啪啪作响。
哦,下雪啦!
小梁睡在炕上,半夜里风大,被子又薄,蜷起腿还是冻得打哆嗦。他刚刚闭上眼,女主人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又浮现于眼前,哪里睡得着?翻来覆去还是难以入睡。
院子里,小推车上的货物被雪霜打得噼里啪啦猛响。
女主人还是放心不下,又一次起身点燃蜡烛,披着上衣,站在当门贴着灶房门缝往院子里细细瞅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事,这才放心往回走,刚走到西间门口,又听见小梁在西间炕上,突然“唉”了一声。
天太冷啦,夜都这么深了,一个人睡在冰冷炕上,再说,今天晚上西间炕上又没有生火。想到这里,她又一次敲门来到小梁的房间。
“大哥,我看天这么冷,炕这样凉,要不?你快到东屋里睡吧!”小梁犹豫之后,觉得不妥就再三推辞,女主人却再三劝道:“你若不嫌弃,快到东间睡吧,东屋炕上今晚生火,暖和得很哩。”
“好妹子,谢谢你的好意,我……我过去不太不方便。”他有点难为情。
“没事的,家里就俺娘俩。”她说话很干脆。
“你……你家大哥呢?”
“他去胶南啦。”她见小梁迷惑不解,又补充“去给队里带工,说什么到胶南打防空洞,一时半会回不来。”
“孩子呢?”
“早就睡啦!”
她见小梁还在犹豫,伸手抱起炕上的被子转身向外走。小梁干瞪眼,只好跟着她也来到东间。
哦,这屋里的确暖和!
女主人把熟睡的孩子推到中间,热炕头让给小梁,自己睡在孩子的左边。
小梁冻得也不再谦虚暖暖地睡在热炕头上,用被子把自己的头部遮住蜷缩着身子,忽然,从被窝里传出一个男人的抽泣声。
“大哥,你这是咋啦?哭啥?”
“大妹妹,你太好了,这么好的心肠,我今生今世也无法报答你!”
“说啥话?没出息。”她停了一会儿,又道:“我问你一个事。”
“啥事?”他停止抽泣。
“你叫啥名字,老家是哪里的?”
“梁光辉,凉台南张洛。”
“奥,你老家有山吗?”
“没有,俺老家全是大平原哩。”
“俺不相信。”
“真的,不骗你,在俺老家锄地,从地北头一直锄到地南头,你想找块石头瓦片擦擦锄都难找不到,不像这里出门就是山。”
“真的?”
“真的,我不骗你,谁骗你出门就死。”
“说啥话?死,死,净说丧气话。”
“哎,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这张臭嘴。”他再三向她道歉,“哎呀,光顾我说话,我还没有问问你的名字呢?”
“凤玉。”
她躺在炕上,瞅着黑洞洞的屋芭,向他作者解释“凤是凤凰的凤,玉是玉石的玉。”
“凤玉?”
“是的。”她干脆地回答。
“多好听的名字呀,俺记下啦!”
……
话说到这个份上,呱越拉越投机,话越说越近乎,不知不觉已是深夜。
蜡烛虽然熄灭,但是两颗心还在咚咚直跳,特别是女主人——凤玉,在西间的烛光下,她上身披着碎花红棉袄……心与心碰撞才能点燃,柴与柴相堆才能燃烧。
小梁好像装着什么心事,翻来覆去,在炕上跟豆虫似的扭动着身子,他丝毫没有一点睡意,胸口扑通扑通跳得厉害,隐隐约约,还感觉到一阵莫名其妙的燥热。他伸开腿脚想放松一下,不小心,一下子碰到凤玉的右脚指,二人触电似的迅速移开。第二次,第三次……慢慢地,两颗年轻的心渐渐碰在一起,正在燃烧,正在爆发,正在跨越那道看不见的堤坝。
霎时间,整个屋子呼吸停止,空气静寂,尽管寒冷的北风在窗外飕飕刮得不停,雪霜子时急时缓很有节奏地敲打着窗户,但还是没有浇灭正在燃烧的干柴与烈火。
风止了,雪停了,小车也修好了。
第二天上午,小梁把身上所有的路费都掏出来,一共是五十六块七,用灯草纸严严实实包好,趁凤玉刚走出房间,他把钱偷偷地掖在被子下面,然后话没说一句,低着头推起货车朝西大路走去。
凤玉肩膀斜倚着门框,眼里噙着泪水,望着这个负心汉背影渐渐地,渐渐地远去。
哦,她的心碎了!
作者简介:张瘦石,年开始散文、小说创作,作品发表于《时代文学》《青海湖》《参花》《散文选刊》《山东教育》《速读》《东方散文》《风筝都》《潍坊日报》《潍坊晚报》《当代散文》等报刊。多次获省市文学创作奖,著有诗文集《潍水悠悠》。
壹点号山东创作中心
本文内容由壹点号作者发布,不代表齐鲁壹点立场。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uimuasm.com/sszz/103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