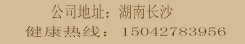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天敌 > 文坛大腕也爱读佛,比如鲁迅,莫言,金庸,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天敌 > 文坛大腕也爱读佛,比如鲁迅,莫言,金庸,

![]()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天敌 > 文坛大腕也爱读佛,比如鲁迅,莫言,金庸,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天敌 > 文坛大腕也爱读佛,比如鲁迅,莫言,金庸,
鲁迅
鲁迅是周家的长孙,极受重视,家人担心养育不大,还未足岁,即由父亲领着去拜他的第一位师父。他们前去的寺庙,是被誉为绍兴八大寺观的长庆寺,孩提时,父毌让他皈依,送去长庆寺拜当家和尚为师,取法名:长根。后耒鲁迅以“长庚”作为芼名撰写杂文《唐朝的钉梢》,就是取其谐音。
目前,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有一个銀八卦,上面刻有:三宝弟子法号长根。拜的师父为长庆寺的主持龙祖法师。龙祖法师替鲁迅取法名为“长根”,师父赠他银八卦一件,上刻“三宝弟子法号长根”,鲁迅还有一件百家衣,即“衲衣”,非喜庆大事不给穿上,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用以避邪。鲁迅年幼时,遇到该寺做水陆道场,都会随家人到该寺去看热闹。
鲁迅一直到他临死的那年,即年4月他还写下《我的第一位师父》的文章(收录在《且介亭杂文末编》),追忆去世已有40年的龙祖法师;鲁迅也推测龙祖法师的徒弟,也就是他的师兄弟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文章写道:“我们(指与他的师兄弟)的交情依然存在,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文情并茂,真挚亲切,显示了鲁迅感情丰富的一面,感人至深。
鲁迅也结识、结交不少是佛教徒的朋友,如许寿裳、许季上,日本人内山完造、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等人。其中与鲁迅交情最深的,当推许寿裳。
相对而言,鲁迅与佛教经典的关系,就甚为密切,且终其一生,都与佛教经典保持善缘。
根据鲁迅日记,他从日本留学归国,于年,在北京担任教育部官员时期,开始大量阅读佛教经典,努力研究佛学。这一年,他购买佛学书籍多达70、80种,占全年购书数量的二分之一,这些佛书有《释迦成道记》、《金刚般若经》、《发菩提心论》、《大乘起信论》、《瑜伽师地论》、《大唐西域记》、《玄奘法师传》、《高僧传》、《阅藏知津》等。
他不但自己看佛书,研究佛学,还不断给绍兴老家寄去佛书。根据鲁迅好友许寿裳回忆,年以后,鲁迅除了自己买佛教书籍,研究佛学外,还与许寿裳订下协议,合购佛书,互通有无,这很可能是基于经济不甚宽裕的原因。
鲁迅不但大量购买佛书,对出版佛书,也作出贡献。《百喻经》,又名《百句譬如经》,古印度僧伽斯那著,是佛教寓言作品,南朝齐时,由印度僧人求那毗地带到中国,并译成中文。鲁迅亲自校对,并出资刻印,可以想见他对此书极为重视,他这样评论该书:“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亦随在可见。”鲁迅也利用刻印《百喻经》剩余的款项,刻印《地藏十轮经》。
许寿裳回忆鲁迅的文章,曾记述鲁迅向他这样剖白:“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金庸
一个人,一支笔造就了一个江湖。金庸武侠小说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奇迹,一个难解之谜。上至政府首脑、文人墨客,学者教授,下至贩夫走卒,从中国到美利坚,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层出不穷的“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有人甚至说他是武侠小说创作的“真命天子”!金庸小说中蕴涵着儒、道、释、墨等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其中尤以佛学为盛。
金庸与佛禅的关系一直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金庸与佛有缘,对佛学有很深的造诣,为了能够直接读懂佛经,他还潜心学习全世界最复杂的文字梵文。金庸先生在与日本著名宗教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讲述了自己皈依佛教的心路。事实上他并非由于接受了哪位大德的接引,而是亲历了非常痛苦的过程。
年10月,金庸19岁的长子查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这对他真如晴天霹雳,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此后一年中,金庸先生阅读了大量书籍,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详细细地研究了一本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怀》,但并不能解答他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康丁霍夫?卡列卢基曾经说过:“在东方,生与死可说是一本书中的一页。如果翻起这一页,下一页就会出现,换言之是重复新生与死的转换。然而在欧洲,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整的书,由始而终。”可能是由于东方与西方的生死观有着本质的不同,金庸先生最终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佛经。
人们都知道金庸喜欢佛经,但很少有人知道金庸是看着英文版的佛经来研读的。金庸说;“我看经书很多时候是看不懂的,我就去看注解,结果,那些唐宋时代的高僧的注解也都很难懂,越看越糊涂,我就只好看英国人直接从印度佛教翻译过来的,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容易了解、接受。”于是,他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的英文译本。对于只看注解,而不去学习经书原文的金庸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这就像手指月亮,原本是为了要看月亮,才看手指的,但有时候看多了手指,只记住了手指,反倒忘了月亮的存在了,实在是要不得的。”一生对佛学颇多研究的金庸先生在他的作品中都临摹过佛教世界,也塑造了众多的佛界僧侣形象。比如《笑傲江湖》之中,仪琳为求令狐冲早脱苦海,念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慈悲之情,发自肺腑;比如《倚天屠龙记》之中,张无忌为救义父与少林三僧苦战,而谢逊于地窖中念诵《金刚经》妙法,劝无忌弃了人我之分,毋着世相。
比如《射雕英雄传》里的《九阴真经》,其实就脱胎于佛教中的经典《愣严经》。而其中着墨最多的当属《天龙八部》。倪匡曾经说:《天龙八部》这个名字就是从佛学中来的,故事中的三位主角和佛教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大理段氏累世信佛,萧峰的师傅是少林高僧,而虚竹则是僧人出身,他于西夏皇城冰窖,以三段《入道四行经》驳得天山童姥理屈词穷,真是言简意赅,仁慈之心,远胜雄辩。这一切,正如陈世骧先生所言:“有情皆孽,无人不冤”,书中涉及的情缘几乎都是“孽缘”,惟一可以例外的似乎只有那位少林寺的扫地老僧。书中融入作者做人、学佛的感悟,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深究佛理的人,是绝对写不出这种书来的。因为同时刻画了金轮法王、鸠摩智等僧门败类。一些评论家认为金庸贬低少林众僧,是不喜欢佛教。但实际上他笔下的恶僧多以不得善终而结局,这又印证了佛学因果报应,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说法,证明金庸不但喜欢佛,更以佛的学说昭示天下。
金庸在和友人的一次论道中曾谈到:中国近代高僧太虚法师和印顺法师都提倡“人间佛教”,主张佛教要入世,要为社会、民众做贡献。即大乘佛教所提倡的“普度众生”,他认为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思想。实际上在他的作品中,对于佛家的“功德”就另有一番解悟。乔峰一生杀人无数,酒量过人,奈何少林无名神僧赞之“菩萨心肠”,被誉为“最有佛性”的人物,保境安民,以一人换两国数十载安宁,正是佛门最上乘之“无畏施”。雕侠杨过,襄阳缄下飞石而毙蒙哥,杀一独夫而息两邦苦战,救万千黎民于水火。此等功德,岂是吃斋戒酒可得?
悟是佛家很玄妙的字眼。金庸说:“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我心灵上最接近‘般若宗’。我觉得开悟之前,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开悟之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金庸这话是说人许多时候看山看水,因为心境的不同,山和水都被赋予了人的感情色彩,等到明白了世间真谛之后,山就是山,水就是水。金庸进一步论证道:“德国康德的本体和现象,其实说的就是这些。”当问及金庸为什么如此喜欢对佛的研究时,金庸解释说:“研读这些佛经之后,我觉得看待许多事情都变得清朗,连死都不怕了,不再计较名利得失,心里坦荡荡的,无所挂碍。”
基于此,金庸以佛教中的“大悲大悯”思想来开导读者,从而增加了武侠小说的思想深度与哲学内涵。难怪北大教授陈平原给予他如此高的评价;“倘若有人想借助文学作品了解佛道,不妨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
老舍
文学家老舍小时候家境贫困,缴不起学费,直到九岁才入学,而促成和帮助他入学的是当过北京鹫峰寺住持的宗月大师。
宗月俗名刘寿绵,系清皇室内务府人,生于富贵之家,一生乐善好施。一天,他来到老舍家,一进门就问老舍的母亲:“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等老舍的母亲回答完后马上表示:“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学钱、书籍,大姐你都不必管!”第二天清晨,老舍就跟着这位刘大叔(即后来出家的宗月大师)上学去了。学校是一家改良私塾,设在一座道士庙的大殿里,大殿供桌上摆着孔子的牌位。刘大叔与一位姓李的老师说了几句,就教老舍拜孔子牌位和李老师,老师当即把一本《三字经》和一本《地球韵言》交给他。从此,老舍就成了学生。
自从当了学生后,老舍经常到刘大叔家里去,那时刘家很阔气,若把他的房子整整齐齐排起来可占半条大街。老舍每次去刘家,刘总是亲切地招呼他吃饭或给他一些穷孩子没见过的点心,从不冷淡这位穷学生。老舍后来由私塾转入公立学校,刘大叔又来帮助他,这时刘的财产已大半施舍完了;老舍中学毕业时,刘什么财产也没有了,仅存一处后花园和一些地产,但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场等慈善事业。这段时间老舍与刘过往最密,曾在刘办的贫儿学校当义务教师,帮助刘调查和发放施舍贫民的米粮。不久刘一贫如洗,落发为僧,法名宗月。他的师父就是当时广济寺的住持现明和尚。
老舍九岁上私塾,三十五年后成了中外闻名的大作家。这时,宗月大师已经与世长辞了。老舍在回顾自己由上私塾到成作家的经历时,特别怀念那位在贫困时真诚帮助过他上学的宗月大师。年1月23日,他在《华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纪念宗月大师的文章,介绍了大师的为人和帮他上学的情况。老舍满怀深情地说:“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也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他是不是真的成了佛?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去入私塾那样。”
老舍曾有过研究佛学的打算。年,他应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邀请去英国教中文,当时著名作家许地山先生(即落华生)也在英国,他是研究宗教比较学的,他在牛津大学的毕业论文就是一篇研讨《法华经》的文章。老舍在教学之余,很想知道一些佛学的道理,便对许地山说:我很想研究一点佛学,但没有做佛学家的野心,请你替我开一张佛学入门的必读经书目录,华英文都可以。许地山为老舍开了一张目录单,介绍了八十多部佛书,说这是最简要不过的,再也不能减少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老舍未能按此计划研究佛学,但这张书目单一直保存着。他曾感慨地对人说:我可知道研究佛经的不易,倘若给我十年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经,也许会懂得一点佛理,但这机会始终都没有。
抗战时期,老舍住在重庆,当时汉藏教理院设在重庆北碚缙云山,一些著名文化人士常到那里去,老舍也曾去那里造访佛教大德,与太虚法师、法舫法师等都有过交往。年4月,他集当时艺术家笔名成一小诗,写成条幅,赠与太虚法师,诗曰:
大雨洗星海,长虹万籁天;
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
诗后附有说明:“三十年四月,集当代艺术家笔名成小诗。大雨诗人孙大雨;洗君音乐家;长虹、冰莹、成舍我、碧野,均写家;万籁天剧导家;林风眠画家。写奉太虚法师教正。”这首诗自然成趣,有幽默感,体现了老舍的文风和他同佛教界朋友的友情。
当年老舍曾应邀在太虚法师主持的汉藏教理院作过一次讲演,题为《灵的文学与佛教》。他以意大利名作家但丁的《神曲》为例,讲了什么是灵的文学,并且从东西方文化交流角度探讨了这部伟大的作品可能受过佛教的影响。他认为《神曲》讲到了地狱的情况,与中国传说的地狱很相像。可是但丁是个天主教徒,天主教所奉的圣经里并未具体说到地狱的情况怎样。信奉该教的但丁却离开了《圣经》,大谈特谈地狱的景况,这也许是他受了东方文化——佛教的影响。老舍还讲到,在中古时候,罗马教皇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者,他的势力比谁都大,谁也不敢触犯他,连皇帝也要双手捧教皇的脚上马,可是但丁却大胆地把教皇活生生地下了地狱,这种思想颇与佛教的平等思想相吻合。当时中西交通已不闭塞,有许多东方的文化输入西方,其中也有些佛学的东西传播到那边去。
老舍在这篇讲演中还讲到佛教对雕刻、绘画、建筑等艺术部门的影响,他颇带感情地说,“佛教与人世间,可说简直是打成一片了。比方有名山的地方,一定就有所宝刹,这种天然之美与人工之美的混合物,在建筑上雕刻上绘画上的艺术观点说来,处处都给予人们的醒目,处处都值得吾人的称颂。讲到建筑,一定先从寺院说起,因为佛徒们已将人间的一切美都贡献于佛了。巍巍庄严的佛像,堂堂皇皇的殿宇,使人看了不期而然的肃然起敬,佛像可以代表中国一部分的绘画。看吧!没有一个名画家不会画观世音菩萨的,谈到我国的雕刻,可说全部都是佛教的。若不是古希腊的雕刻传到印度,由印度传到中国,西洋的近代雕刻画也许不会输入中国的。故从这三方说来,中国的雕刻、绘画、建筑都离不开佛教的。”(《灵的文学与佛教》,载《海潮音》第22卷第2号,年2月重庆)老舍的这番话虽然不长,但可以看出,他的知识是那样的渊博,他对佛教同艺术的关系曾作过思考和探索,他是有见地的。
徐志摩
“五四”作家中,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接触佛教文化:李叔同和苏曼殊本身就是僧人,许地山与丰子凯是居士,梁启超是热情的佛教团体领袖,陈独秀、胡适、鲁迅、瞿秋白、周作人、郁达夫、老舍、宗白华、夏丐尊等都与佛教文化有脱不开的深层关系。
徐志摩与佛教的亲近度不如上述作家,但是佛教特别是禅宗教义的印痕时常在他的诗文中出现,从中也可以看到诗人的另一个精神层面。
徐志摩与佛教的因缘主要来自于家庭的影响,他生于一个虔诚信佛的家庭,周岁时一个叫志恢的和尚抚摸了他的头,为了志恢和尚“必成大器”的预言,在他留美赴学前夕,更名为“志摩”。徐志摩深受西方科学的影响,一生不信奉任何宗教,但从小耳濡目染,佛教特别是禅宗教义对他以后的成长和诗文创作有着一定影响。
禅宗重视对人生精神领域的探讨,认为众生具有先天的“赤子之心”,所谓“一切众生,皆有佛心”。因此徐志摩屡屡赞美童心的纯真和自由,他说:“孩子的身体虽然小,他的灵魂却大着,他的衣服也许脏,他的心却是清净的。”他痛感自己作为成人,早已失去了童心,“有的则是一个年岁与教育蛀空了的躯壳,死僵僵的,不自然的。”(《海滩上种花》)。他感伤自己“是个自然的婴儿,闯入了险峻的城围”。(《我是个无依无伴的小孩》)。
诗人赞美童心,眷恋自然,主要是厌恶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不满诡诈、倾轧、怨毒的时代病象,无法适应当时主流文化界的革命情绪,因此总想飞出这圈子,“飞到云端里,超脱一切,扫荡一切。((《再剖》)。而禅宗教义极力抨击世俗社会的“客尘”、“妄念浮云”的教义,和诗人渴望在宁静的自然中寻求解脱的心态相吻合,使诗人和禅宗“一念净心”的生活态度自觉或不自觉契合到了一起。
禅,作为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一部分,曾深入地融入历代文人的精神和文字间,不管是古典诗文中所描述的那种禅境,还是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渗入的那种禅意,都加深了文学作品更高层次的艺术品位与审美意识。
禅是难以言说的,但又不是完全的不能言说。
表达禅可以言说的语言形式,莫过于诗。因为诗的含蓄,诗的隽永,诗的韵味,诗的非逻辑反理性思维,都使禅的表达成为可能。同样,诗歌在与禅的接触中,吸收了禅对生命,对自然,对山河大地万事万物那种超然、明净、空灵、穿透的智慧和精神境界。诗人在这种境界中,也就成了“诸法无我,明心见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禅者。
在徐志摩的两篇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对禅的理解,这就是散文《天目山中笔记》和散文诗《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
《天目山中笔记》头一句“山中不定是清静”:有松声,有竹韵,有啸风,有鸣禽——“静是不静的”,虽然有“声”,但因为是天籁,不污人耳聪倒使人心宁意远,不静反是静。“声”之后写“色”——目所能及的一切:林海,云海,日光,月光和星光,并非纷扰熙攘的百丈红尘,故而人处其中自在而满足。他在对山中钟音一番颂赞之后感叹:“闻佛柔软音,深远甚微妙”。
禅,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命体验,有着很强的心灵净化功能。以禅的眼光看世界,则超越了世俗的知见和情欲,达到“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随缘而不为物扰的自由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也即禅悟所得之境。
诗人由宏大微妙的钟声联想到了打钟的人。钟是昼夜不歇、片刻一次的,打钟的和尚也已不间歇地打了十一年,连每晚打坐安神也挽着钟槌;他脸上看不出修行的痕迹或失眠的倦态,倒有自在的笑意;不刻意念什么经更或竟不识字——这使我们想起了佛陀在《经集》中所云:“那些超越疑虑,背离苦恼,乐在涅槃,驱除贪嗔,导向诸天世界的人,乃是行道的胜者。”这种“胜者”,也是“圣者”。这里,禅宗的宁谧圆融正是徐志摩所追求的:“‘闻佛柔软音,深远甚微妙。’多奇异的力量!多奥妙的启示!包容一切冲突性的现象,扩大霎那间的视域,这单纯的音响,于我是一种智灵的洗净。”(《天目山中笔记》)
在这里,徐志摩是个回归自然的诗人,是个忏悔者,是个回头的浪子,是佛与魔在内心交战的逃离色界的囚犯,也是一个禅者。徐志摩用禅学思维方式去了悟大千世界,进而了悟文学,他所推崇的理想,正是包含了爱和美的禅性。在他看来,文学的功能在于观照生命,恢复人的生命的自然状态,或唤起这种自生形态的原初体验,使人的生命力得到恣情伸展,这也是禅所追求的境界。
徐志摩一向被视为是一个情感充溢的诗人,这固然是对的,但此文也可以见出诗人心灵的又一层面。我们这样说还有另外一个例证,那就是志摩在其散文诗《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中对佛音梵呗的顶礼和咏赞。
年,徐志摩随陆小曼来到常州,听闻天宁寺的梵呗唱诵,写下《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诗中“我听着了天宁寺的礼忏声!这是哪里来的神明?人间再没有这样的境界!……这一声佛号,一声钟,一声鼓,一声木鱼,一声磬,谐音盘礴在宇宙间解开一小颗时间的埃尘,收束了无量数世纪的因果;这是哪里来的大和谐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在这里,神性和诗性进入心灵得以敞亮,它是“星海里的光彩,大千世界的音籁,真生命的洪流”,庄严静穆的降临,是灵魂在瞬间瞥见的澄明之境:青天、白水,绿草,慈母般温软的胸怀。人在日常沉沦中失落的本真重新显现了,我们窥见了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是故乡吗?”是的。
禅与诗的结合,有其内在本质上的必然性。二者都面对着一个根本的大问题:生命。二者的发生和圆满也都基于同一种情况——觉悟。美在生命的文学理想,无不与禅宗的觉悟哲学相契合,这使我们在感受到诗人敏锐的艺术触觉和强烈的艺术感受力之外,亦能感受到其所倡扬的宁静自由的“禅心”。
文学与禅之所以能走到一起,那便是“悟性”这两个字。
这首诗赞美的对象是美学的,也是宗教的。因为当诗人把我们带入这个静的澄明之境时,我们不仅是感动与共鸣,着迷和倾倒,也在揣摹那动与静对比中静的“神明”,得到某种超度或救赎,而又情不自禁地被带入实在生活之外那庄严、和谐、静定的境界。读这首诗,我们在赞叹“诗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种宿命的力量在回荡,那锣声是世界死寂后的回响,人的灵魂仿佛在等待审判,礼忏声中的锣就这样响过诗人的心头:该忏悔了,该忏悔了!
《天目山中笔记》和《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已经接近了这样的“禅境”。
徐志摩的诗文具有很强的性灵意识,时常会有禅意跳出。在《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一诗中,诗人的文字成为一条光明的小河,小诗《无题》则有了清明的理性,看《苏苏》中“那长夜的慰安,看星斗纵横”犹如看到了一位禅者的参悟。正如沈从文评论徐志摩的诗歌:他的诗“带着一点儿虚弱,一点儿忧郁,一点病,有《在那山道旁》一诗。使作者的笔,转入到一个纯诗人的视觉触觉所领会到的自然方面去,以一种丰富的想象,为一片光色,一朵野花,一株野草,付以诗人所予的生命,如《石虎胡同七号》,如《残诗》,如《常州天宁寺闻礼仟声》,皆显示到作者性灵的光辉。”(沈从文《论徐志摩的诗》)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到剑桥文化的洗礼,徐志摩对禅宗思想的吸收,只是在寻找和谐的层面,并未上升到对佛教因果缘起的本体论的接受。徐志摩诗文对禅的表达,也是很不充分,不成系统的,其成就不仅远不及唐诗中王维、李白、张若虚等诗人达到的禅的意境,也不如现代作家中的许地山、丰子凯这样的作家。《天目山中笔记》和《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在志摩的整个诗文中可以看作是“鳞爪”,但读者可在其中约略看到诗人的探索。笔者认为,如假以时日,随着当时政治环境变化而引发的思想、情感的内敛,志摩的诗文的思想深度和风格或许会有大的变化,这在这两篇诗文中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莫言
年9月15日下午,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台湾高雄佛光山大觉堂与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对话,以“看见梦想的力量”为题,分别从“文学家的梦想”、“宗教家的梦想”观点出发,同台交流,共谈梦想的力量。莫言获聘佛光山首位佛馆驻馆荣誉作家。
莫言此次是应星云法师之邀而来台湾,他自我解嘲说:“都说吃人家的"嘴短",虽在佛光山只有素食吃,但我还是要说说佛光山好。”莫言说,佛光山把佛教精神变成了空气,变成了水,让善念根植到每一个人心中。于是,星云法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就能深入到民众生活中。
其实莫言在作品中也颇多对佛经的直接引用,创作理念中对“道”的借鉴也可圈可点。《生死疲劳》开篇就以佛经“生死疲劳,从贪欲起”看人性,莫言认为这个故事不只是谈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更是着眼于人类一切根本的悲剧──欲望。
莫言表示:“人,当然有他正当的欲望,如果没有正当的欲望,人类社会也不可能延续。但也正由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控制,欲望变成贪欲,变成了无底洞,各类负面现象就层出不穷了。”而为让自己的欲望不变成贪欲,莫言选择宗教精神家园来规范。“佛光山,是我可以安放精神的家!”莫言说,精神的家,要比有一个可以安置身体的家重要许多。“因为一个人精神有所寄托,他所有行为就有准则,就不会无所忌惮了。”
星云法师曾送给莫言一幅书法写着“莫言说尽”,极富禅意。“法师好像告诉我不要再说了,因为说太多了而说尽了,但大师又好像在鼓励我要一直说下去,因为没有说尽。”今后自己的创作之路,要回味再三,拿捏“莫言说尽”的尺度。
莫言感慨说,自己是佛法门外汉,今生虽不能落发为僧,但多读佛典,多结佛缘。尤其回大陆,要好好研究星云法师的佛学著作,从头学起。莫言还表示,自己的房子正在装修,未来将把法师赠与的书法高挂在书桌后,“作为人生谏言”每日提醒自己。
余秋雨
以下文章为余秋雨撰写——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固有门类相比,佛教究竟有哪一些特殊魅力吸引了广大中国人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在学术上很冒险,容易得罪很多传统的文化派别。但我还是想从存在方式上,谈谈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
佛教的第一特殊魅力,在于对世间人生的集中中科医院曝光白癜风医学基金会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uimuasm.com/sszz/17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