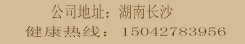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形状 > 诗界NEWS第004期丨莫言出来一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形状 > 诗界NEWS第004期丨莫言出来一

![]()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形状 > 诗界NEWS第004期丨莫言出来一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形状 > 诗界NEWS第004期丨莫言出来一
博渊阁年度精品诗歌年鉴《青风》开始征稿了,各位诗友抓紧时间投稿哦!
点击[了解详情]
莫言:出来一趟太紧张到处都在拍你到处都在录音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5年,莫言没有发表新作,也鲜少露面这一回,
钱报记者贴身跟了他五个半小时——
莫言:出来一趟太紧张了到处都在拍你,到处都在录音
莫言。中新社记者韩海丹摄
年8月23日,晴,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
这一天,第24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刚刚开幕。
就在莫言现身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同一天,另一条与他有关的新闻也在朋友圈里热传:莫言的新的三个短篇小说,将要在新一期的《收获》上一道发表。而刚上市的年第9期《人民文学》上,刊登了莫言的戏曲剧本《锦衣》和诗歌《七星曜我》。
下午1点45分,作家莫言亮相。
这是一场圆桌会,主题被投影在舞台背景墙上:那是一张莫言在网上最常见的照片,旁边写着:故事沟通世界:莫言对话30国汉学家。
莫言坐在背向舞台最中间的位子上,事实上,在没有位子的“观众区”,能看清的,也只有背向舞台的这一排座位上的嘉宾。
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里,开一个被许多人围观的圆桌会议,场面其实是有些怪异的。观众区越来越多的人和嘈杂的声音渐渐让会场的音响都显得有些无力。为了防止人太多,保安早早将整个区域用隔离带围住,只让出不让进。
“我首先考虑的是本国的读者”
即使进入了活动尾声,但现场的30位汉学家对莫言的发问热情有增无减。
有人问:“我们见过黑狗、红狗,但您小说里提到过一种绿狗,那是什么?有什么含义?”
莫言回答:“我记得有一个小说里,一个孩子问母亲要一匹马,母亲问他要什么样的马,孩子说要一匹绿马。母亲说,这个世界上有白马有黑马,但就是没有绿马呀。但孩子一定要绿马。我想说的是,作者有时是会与生活作对的,无论是绿狗还是绿马,都是想让读者感到与常识的冲突。作者有时是会带着儿童的执拗和恶作剧的心情。”
莫言。中新社发阮煜琳摄
又有人问:“您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是否会感到应该对读者负责,特别是对外国的读者?”
莫言答:“我们总会说写作的时候要忘掉读者,毕竟读者成千上万,过多地考虑如何去适应读者的口味,会让作者变得无所适从。您所说的担忧和责任固然存在,读者对你的期望很高,期望你有更好的作品。这对作者会形成很大的压力,也会很难把握。在没获奖前,改到觉得差不多了,就发了。但现在是再放放,再放放。如果非要说考虑读者,我想我首先考虑的也是我们本国的读者,而不是国外的读者。我自己对小说有追求完美的愿望,对小说艺术有着病态化的热爱,我所希望的是写出让自己得意的作品,这比任何奖项荣誉都更让我满意。”
有人问:“您会不会觉得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完了?”
莫言说:“一个人一生经历有很多,任何一个作家都不会说自己已经说完了自己想说的。年我去台湾,和星云法师见过一次面。他给我写了一幅字,上面写着‘莫言说尽’,很有禅意——一方面可以理解成还没有说尽要继续说,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成说的时候注意,不要说尽了。”
莫言的回答都是紧接着问题,中间几乎没有任何思考的停顿。
但是,一个穿着红衣服的秘鲁女记者,提出了一个似乎终于难住莫言、甚至难住在场每一个人的问题:“莫言老师,我想请问您,爱是什么?爱情是什么?”
莫言笑了:“你听,大家都笑了。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得考虑考虑。但我知道秘鲁,那里有种土豆,我爱吃土豆,所以如果问什么是莫言的爱?土豆!”
“嗓子哑了,就不接受采访了吧”
时针指向2点,在一片笑声与掌声中,主持人宣布活动结束,嘉宾合影。然而观众区的人早已迫不及待,拿着书冲上舞台向莫言索要签名,但被保安一一拦住。而我和下一场活动的主办方代表之一、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一道,被挤到了舞台边缘。看着莫言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郑重无奈地苦笑了一下:“所以这些年他也很少出来。”
从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已经有5年的时间,但莫言在公众面前所引起的轰动效应显然并未随时间衰减。甚至也许正是因为自获奖以来,莫言很少出现在公众场合,才引起了大众对他加倍的好奇。
下午2点05分,在四名保安的帮助下,莫言得以从人群中出来,前往下一个活动现场。
莫言走的这条路,是郑重事先踩过点的:“这条路比较宽,人也比较少,虽然可能要稍微绕一下。但是没办法。”
郑重跟在莫言身边,我跟在郑重身边。四位保安把我们围在中间,努力地开出一条畅通的走道。我看了一眼身后,有好几个抱着一大摞书的人紧紧地跟在后面。
“莫言老师!我是XXX媒体的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莫言老师帮我签个名吧!”
“莫言!是莫言!快跟上去看看。”
跟上来的人越来越多,周围举着手机拍照、录像的比比皆是。
与刚才在座谈会上侃侃而谈的状态不同,莫言紧闭着嘴唇,一路一言不发。他走得很快,使得前面的保安有时还不得不往前小跑两步,挡开前面的人。
5分钟后,莫言抵达了浙江出版集团展位的休息区。刚一坐下,就有人挤到他身边拿着书要求签名。保安在一边轻声对着对讲机说:“请求支援。”
莫言将随身的小包放在桌上,拿起一瓶矿泉水,拧开就喝。
有人又递进来两瓶水,莫言晃了晃手里的水瓶,表示这儿有水不用了。
也有几家媒体挤进来想要对莫言进行采访,莫言指了指自己的嗓子,说:嗓子哑了,就不接受采访了吧。
“你们就让莫言老师歇会儿吧。”坐在莫言对面的郑重对着周围的人说。
很快,现场的保安增加到了6个。
“现在出来一趟太紧张了”
两个小时的沙龙对话十分精彩,周围有许多人是站着听完了整场沙龙。
与前面一场活动一样,主持人一宣布活动结束,人就从四面八方涌向了舞台。最后,还是在保安的帮助下,莫言才顺利进入相对封闭的休息室,接受了三家媒体的采访。
尽管很少参加一些公共活动,但莫言今年还是参加了一个文学奖的评审工作。
“评奖过程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个读者,我要把组委会给的作品都通读一遍,才能评出最好的作品。这是个享受,是逼着你做个认真的读者。我其实没有做过太多的评委,就只有今年的京东文学奖,但看到了宝刀未老的老作家,看到了非常成熟的80后作家,看到了初露锋芒崭露头角的90后作家。如果非要说一些不同寻常之处的话,我们山东高密,出现了一个90后写作的小群体,让我这个高密老乡很欣慰。高密这个小小的县级市,居然有小的文学群体,我相信现在中国有个广大的写作群体,文学大军。”
临近5点,所有采访基本结束。这时有人进来说,外面有一群河北来的小朋友,想要跟莫言说几句话。“进来吧,那就。”莫言笑着说。四个穿着红背心的小女孩抱着采访本小心翼翼地进来了。第一个小女孩说:“莫言爷爷您好,我想问您个问题。”莫言说:“你说。”小女孩说:“您觉得您的哪部作品比较适合选进我们中小学生的教材呢?”莫言笑了笑:“还是别选了吧。”接着又一个小女孩问:“莫言老师,请问您获得诺贝尔奖时是什么心情?”莫言回答:“就跟见到你的心情一样高兴。”
四个小女孩美滋滋地得了签名照合了影,蹦蹦跳跳地出去了。
当所有媒体镜头都撤去时,休息室里的莫言才松弛下来。他说:“现在出来一趟太紧张了,到处都在拍你,到处都在录音。”
下午5点19分,在保安的护送下,莫言来到了展览馆的停车场,在周围工作人员忙碌地确认来接莫言的车子是否到位的时候,莫言忽然说:“今天的云很漂亮啊。”
来源:钱江晚报
诗界NEWS
诗界资讯,一手掌握,让生活离诗歌更近一步!
莫言复出,多了从容和温情
“锤子凿子,叮叮当当/石片飞溅,目光荒凉/爷爷提醒过我:看狗拉屎也不看/打石头的”———你读过小说家莫言写的长诗吗? 眼下,国内首位诺奖得主莫言全面复出。记者昨天获悉,除了最新短篇小说将亮相九月中旬面世的第五期《收获》,新鲜出炉的今年九月号《人民文学》杂志首次开设“莫言新作”专栏,最新戏曲文学剧本《锦衣》、组诗《七星曜我》 无不展示了作家莫言在不同文学体裁上的尝试、跳跃。
全面复出的莫言“花开多枝”,最新戏曲文学剧本《锦衣》、组诗《七星曜我》首发于刚上市的九月号《人民文学》,最新短篇小说将亮相九月 中旬出版的第五期《收获》。(人民文学杂志社供图)
同样在昨天,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BIBF) 开幕,莫言现身的“中国文学与全球化时代———莫言作品国际传播沙龙”,云集了来自阿尔巴尼亚、缅甸、保加利亚、以色列的翻译家及汉学家,他们译介过莫言《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蛙》等小说的不同语种。莫言在现场说,他愿意邀请所有翻译过他作品的译者,到他的老家高密走走。
“无论是莫言的文学姿态,还是他在组诗中与世界对话,都不是简单地‘走出去’,更是一种对外界积极开放的打量和观照。”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用“从容”“谦逊”来表达他对莫言新作的感受。业内关于莫言,曾有“以磅礴的语言气势制造并维持了泥沙俱下的高产,让读者喘不过气来”的说法。近年莫言在盛名之下不断寻求突破,“这很不容易。如今莫言的诗歌、散文和戏剧多了一分从容、放松和坦荡。许多成名作家都会有不从容甚至焦虑烦闷之时,只不过往往以持续的高产掩饰过去罢了。现在莫言新作告诉读者,尽管他的肆意挥洒一如既往,自信也一如既往,但其中多了一分谦逊和大度。比如,不再单纯依赖小说,而挺进诗歌散文和戏剧领地,路子走宽了;比如,不再纠缠于过去他自己提出或别人帮着提出的口号,而寻求字里行间的淡定;比如,夸张狂欢一如既往,但多了一分平实和素朴。”郜元宝说,目前判断莫言仍在徘徊还是迎来新的喷发期为时尚早,但他期待莫言能真正找到从容叙述的心态和调子,同时也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景带来令人振奋的理由。
“千呼万唤始出来”,莫言的一系列新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突破或拓新了他已有的文学资源,似乎还很难说;至少,从字里行间看,他所迷恋的“故乡”“石匠”“铁匠”等意象依然顽固,在莫言体内仍蛰伏着一头精力十足的语言野兽。
野兽,出栅了。
剧本《锦衣》:“故事只是酒杯容器,真正的酒精度集中于语言本身”
“好作品才是作家的‘王道’。这足以表明,不是‘莫言回来了’,而是‘莫言一直在’。”《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告诉记者,小说之外的文艺样式,尤其是民间文化与民间文艺,向来是莫言创作的重要资源。“剧本《锦衣》 中,莫言的语言更自由老到,文笔也讲究结实些。过去他写故乡、大地、人物,总抑制不住一种冲动,要往天上飞;现在,莫言更多往大地上扎根,更注重生命的伦理。当然两种写作都有优点,莫言当下的调整,感觉上更接近其本心。”
纵观莫言的创作图谱,剧本是整个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话剧《霸王别姬》与《我们的荆轲》都曾有过热烈反响,小说《檀香刑》就有莫言对故乡一带地方戏种茂腔的悲凉婉曲之风的成功化用,而他获茅盾文学奖的《蛙》后一部分,则是标准的多幕话剧。
到了最新戏曲剧本《锦衣》,自然展现了山东戏曲茂腔、柳腔的唱词和旋律特色,但又不局限于地方戏的表达时空的设定。“民间想象、民间情趣与历史关节、世道人心活化为一体,一个个人物的表情、腔调、动作和心理形神兼备于文本的舞台。”施战军评价道,《锦衣》回归了莫言拿手的“民间叙事”,有所区别的是,以往莫言笔下的石匠、铁匠、货郎、民间手艺人带着较为浓重的先锋性,文本受观念驱动的痕迹明显,现在更多以情感取胜。
《锦衣》的剧本核心,融合了“公鸡变人”的民间传说、动荡年代下的恋爱等题材。青岛科技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赵坤说,《锦衣》在形式自由的地方戏里,随着调子、声气、运腔的婉转高昂,是最放达的民间想象,也是生动的人类表情。在青年评论家李壮看来,如果说“讲故事”的行为在根源处包蕴着叙述者对叙事规则本身的遵循与突破、妥协与冒犯,那么今天的莫言,则几乎已经跳脱出这一枝杈横生的框架:在他这里,故事本身仅仅是途径或者说工具,是布满老茧的手掌中跨江的溜索,是盛满琼浆烈酒的高脚玻璃杯———“对影成三人”的微醺永远是酒精的魔术,谁也不会把盛酒的杯子认真吃下肚去。
“故事只是酒杯容器,莫言新作中,真正的酒精度集中于语言本身。我们不妨将它看作是一场韵律的狂欢、一次语言天赋的尽情挥洒。”李壮说。
在戏剧的结构和人物塑造上,《锦衣》全面向传统戏曲复归,如单线的叙述、起承转合的情节走向、写意的动作和装置、大团圆结局等。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兵分析说,从《霸王别姬》到《我们的荆轲》,从《檀香刑》里的茂腔悲风到《蛙》结尾处九幕话剧的一咏三叹,再到最新的 《锦衣》,莫言正一步步实现着自己“作为戏剧家的野心”。“显然,他更青睐于在民间发掘戏剧质朴的力量,并尝试对旧戏和民间戏曲的审美创造性转化,使之成为当下戏剧创作的源头活水。”
时隔13年再次“三弹齐发”短篇,不由自主又写铁匠
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分外耀眼,似乎也带来一些“不能承受之重”。诺奖傍身五年来,作家莫言的创作在外界强烈 8月18日,上周五,这天距离《收获》杂志第五期下印厂只剩几天,所有篇目处于审读校样的最后阶段,这一期也是收获创办60周年的特别纪念刊。清晨六点不到,《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我在故乡,写了三篇小说,想发给《收获》看一下。”短信来自莫言。在江苏如皋接到莫言来稿后,程永新一口气读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评价:“三个短篇组成一个系列,不到两万字,人物鲜活生动,题旨涉及故乡土地和童年记忆,精神气息与莫言以前的作品有相通性,这组短篇都不长,稍有变化的是语言,准确、精到、节制,长句子少了,明显是精心打磨的作品,标志性的通感艺术手法运用依然得心应手。”
在短篇小说正文前的“小引”中,莫言写道:“各位读者,真有点不好意思,我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里,都写过铁匠炉和铁匠的故事。在这篇歇笔多年后写的第一篇小说里,我不由自主地又写了铁匠。……”为什么莫言这么喜欢写铁匠? 其中包含了成长经历中哪些魂牵梦绕的场景?苏州大学教授、评论家王尧告诉记者,三个短篇,都与莫言青少年的经验有关,但超越了他的个人经验和故乡人事。“新短篇系列重构了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有既往的延续,但更多的是在故事中重新发现人性的秘密,在肌理处呈现乡村社会的场景。小说在不经意间,沉潜了莫言的人生智慧。莫言讲述故事的才华依然文气沛然,叙述疏密适宜,更多了从容、淡定和温情。”
莫言曾说过,故乡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扩展的。“作家往往有着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能力。乡土是无边的。我有野心把高密东北乡当作中国的缩影,我还希望通过我故乡的描述,让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经文学发酵后,高密东北乡在莫言笔下成了“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这并不是莫言第一次以“三弹齐发”的强烈风格化登上《收获》。13年前,年第三期《收获》上就曾同时发表了莫言的三篇短篇小说 《挂像》《大嘴》和《麻风女的情人》,引起评论界瞩目。自年第五期首发他的中篇小说《球状闪电》以来,《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师傅越来越幽默》等十几个重要作品悉数在《收获》首发,长篇小说《蛙》首发在年第六期《收获》上,于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翌年问鼎诺贝尔文学奖。“通常杂志短篇不用插图的,但美编喜欢老莫的小说,一连画了三幅,现在是每个短篇都有插图和莫言的书法题名。”程永新说。
组诗《七星曜我》与世界文学对话,惺惺相惜中透着开放包容
君特·格拉斯、勒·克莱齐奥、帕慕克、奈保尔、大江健三郎、马丁·瓦泽尔等七位知名作家,被写进了莫言的组诗《七星曜我》中。“这组诗,一般作家很难写出来,与多位国际知名作家的交往,融合在诗句的意象中。”施战军说,组诗《七星曜我》以独特的才情与见识,与当代世界文学大师对话,这更像是一种隐喻:今日世界格局中,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文学的影响空间也变得日渐阔朗和通透。
无论是戏曲剧本还是组诗,都在亦庄亦谐中富含着中国智慧和文化自信。借助戏曲唱词和诗歌的形式,莫言完成了一次“语言的自我提纯”———那些原本与小说故事交缠在一起的语言冲动,由此获得了自足而绝对的呈现,最后干脆摇头晃脑地唱了起来。(许旸)
来源:新浪网
诗界NEWS
诗界资讯,一手掌握,让生活离诗歌更近一步!
莫言打破沉默BIBF图博会速报
最近有关莫言的消息很多,与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身份关系不太大,而是回到了作家的本职工作——写作。获得诺奖五年后,莫言终于有新作面世。
本周,《人民文学》杂志和《收获》杂志都发出消息,莫言的新作品即将刊发。《收获》刊登的是莫言三个短篇小说。8月18日,距离新一期《收获》下厂印刷只有几天的时间,主编程永新收到莫言发来的短信:“我在故乡,写了三篇小说,想发给《收获》看一下。”程永新一口气读完,“三个短篇组成一个系列,不到两万字,人物生动,语言与老莫以前的比,节制,精到,准确,长句子少了,明显看得出是经过精心打磨的作品,依然把通感的艺术手法用得得心应手。”篇名和内容暂未被透露,据悉三个故事仍然是关于故乡、关于铁匠的。“那个放松的、幽默的、最会讲故事的莫言,别无分号,别来无恙。”《收获》负责人告诉记者。
《人民文学》9月号将刊登莫言的戏曲文学剧本《锦衣》和一组诗《七星曜我》,均由莫言本人题写篇名。主编施战军在卷首语中提到,无论是剧本还是组诗,都在亦庄亦谐中富含着中国智慧和文化自信:“《锦衣》自然而自由地展现山东戏曲茂腔、柳腔的唱词和旋律特色……组诗《七星曜我》更像是一种隐喻:今日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文学的影响空间也变得日渐阔朗和通透。”施战军不同意这是莫言的“回归”,“不是"莫言回来了",而是"莫言一直在"。”
莫言还于本周三亮相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出席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文艺出版社举办的“中国文学与全球化时代——莫言作品国际传播沙龙”等一系列活动。他和各位汉学家、翻译家坐在一起,也和读者离得很近,活动结束有工作人员要求合影,他也愉快地答应了,像一个随和且心态开放的老头儿。
活动主题和莫言作品的海外输出有关,阿尔巴尼亚翻译家伊里亚兹·斯巴修、缅甸翻译家杜光民、保加利亚翻译家韩裴、以色列汉学家、翻译家科比-李雅各讲述了翻译莫言作品的经验与心得。有专家总结说,这些小语种译本,是中国作家在国际语境中“打破沉默”的一种见证。莫言在发言中表示,自己年轻时深受外国文学影响,他觉得中国作家未来有希望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自己的位置。“我想,只要我们的作品不断地被翻译出去,假以时日,总会有国外的作家和年轻人,从中国作品受到启发的。”当然,他给这个美好的祈愿加了个前提,“只要我们努力地写。”
来源:BIBF图博会速报
诗界NEWS
诗界资讯,一手掌握,让生活离诗歌更近一步!
往期:
诗界NEWS(第期)丨中国诗歌学会召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会
诗界NEWS(第期)丨《中华好诗词》第五季正在热播浪漫七夕主题本周上线
诗界NEWS(第期)丨中国诗人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演讲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uimuasm.com/ssly/4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