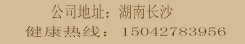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种类 > 金英夏短篇小说密会下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种类 > 金英夏短篇小说密会下

![]()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种类 > 金英夏短篇小说密会下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种类 > 金英夏短篇小说密会下
密会(下)
作者:金英夏(韩)
译者:浪漫松果
J.S.巴赫鲁特琴组曲No.1,BWV:萨拉班德,
演奏者:JulianBream
每年秋天,我都会来法兰克福。如果说只为见她而来,那当然是撒谎,其实我是为购买著作权而来。十月,在法兰克福会举办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图书展。在那儿,乘坐热气球环游世界者的故事,从罗马横穿至北京的徒步客的游记,日本出身的世界级理财专家的著作,皆被我购入囊中。如今想想,真是奇怪,我买的书里无一不充斥着生活炽烈的人们。他们要么从北极至南极沿着同一经度旅行,要么拼上全部身家囤积财富。人们似乎对比自己活得勤奋、疯狂的人生故事,尤为热衷。殊不知,这种生活其实真的很疲惫。滞留法兰克福的三天里,我与代理商、出版界人士、猎头们会面,精疲力尽。
图为法兰克福图书展
接着,我不会马上返回首尔,而是来海德堡再呆上几天。每逢那时,我都会与她见面。在内卡河畔的长椅上,我读着从书展拿来的样品书,而她则枕着我的膝盖,安然入眠。我拿起事先准备的涤纶毛毯,给她盖上。这一刻太过美好温馨,不知为何,总感觉像从他人的人生里悄悄借来一般。我们像害怕被人发现的小毛贼,小心翼翼地珍惜这一时光。
啊,她终于离开那座古老的桥,向着宾馆走去。宾馆位于桥前。她拉开黄铜扶手,走进宾馆。接着,拾阶而上。咯噔咯噔,嘎吱咯噔。木梯的声音深情地传来。我总是梦想住进装有木梯的房子,却从未实现。我只在平房和公寓里生活过。默默承受人体的荷重、悄悄发出呻吟的木梯,我从没能有过。也许正因如此,我才选择了这座宾馆。“都什么年代了,连个电梯也没有!”她嘟嘟囔囔,却更中我意。如果能再出生一次,我想要做一棵树,作为树的生命完结后,我希望成为木梯。
图为内卡河畔
“你丈夫怎样了?”
虽然她讨厌这个问题,但我每次见她,总会从这个问起。她的丈夫脖颈粗短,身材矮胖,是一名业余摔跤手。这个世上居然还有爱好摔跤的人,我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听说他本是安养一所初中的英语教师,却比起英语来,更喜欢指导摔跤部。向学校提议开设摔跤部的人,也是他。也许是因为指导教师的热情,该校摔跤部创建不到几年,便在全国少年体育比赛中获得了亚军。放学后,他也经常和孩子们一起练习摔跤。听说他爱学生,尤为疼爱其中的一名。那个孩子的父亲是名公交车司机,从初二时起开始练习摔跤。他运动神经发达,头脑也好,很快便崭露头角。人们认为摔跤是力量为主的运动,但实际上判断力也十分重要,并不亚于体力。在其他同学都回家后,那个孩子仍在垫子上翻来滚去,反复练习。她的丈夫便成了孩子的陪练,一起流汗苦练。就那样,某一天,事情发生了。准确来说,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两人都说,仅仅是进行了日常的陪练。只是,孩子使出的招数准确击中,丈夫的身体弹向虚空,在没来得及准备好的情况下,身体落到了垫子之外。虽然头撞向地面时疼得厉害,但他想,哪能在弟子面前喊疼?于是,马上掸了掸,站起身来。
“不错嘛”,
类似的话也许从他口中脱口而出。据说,孩子们偶尔会有过度好胜的倾向。这种练习的时候,也全力以赴想要赢得对方,稍显危险的技术也会果敢采用。也说不定,孩子使出如此厉害的招数,是有着不为人知的隐情。不管怎样,她的丈夫开着车,平安无事地回到家中。接着第二天,一觉睡到了晌午。醒来后,他感到了轻微的眩晕和头痛。然而,这对运动的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便没放在心上。几天过去,头痛和眩晕消失了。
然而,又过了几天,奇怪的事情一桩接一桩地出现。丈夫开始在外面过夜。她四处打听,结果在家附近的旅馆里发现了丈夫。他独自起了床,正在刷牙。没有女人睡过的痕迹。
“怎么回事?”
不管她怎样追问,丈夫就是不回答。几天后,她找到了平时和丈夫颇为亲密的学校同事——常和丈夫就着五花肉喝烧酒的国语老师。他一见到她,便一脸尴尬。她凭直觉感到,发生了一桩极其重大、难以轻易解决的问题。
“我没事的。告诉我吧。”
同事一连干搓着脸,困惑极了,终于开口道:
“赵老师有些怀疑您。”
“什么?”
“啊,不是那种怀疑。他觉得,自己的太太换人了。”
“这是什么话?”
“他也知道这不像话,自己也很痛苦。照他的话说,真正的妻子去了别处,假妻子模仿真妻子,呆在家里。”
“他疯了。”
“那倒不是。上课或其他事情都没有任何异常,好好的。”
她说,自己没有哭。国语老师反而更加尴尬,就在继续谈话的时间里,她坦白有一刻想起了我。
“哎,不知道对您算不算得上是安慰。”
她抬起头,望着国语老师。
“请说。”
“他也在怀疑我。”
“他亲口说的吗?”
“不。可总感觉不像从前。很多时候就像对待陌生人。不管怎样,医院……”
她说服丈夫,把他从旅馆带回了家。可是,丈夫就像对待陌生人,换衣服的时候也会锁上门,更没有一句温存的话。无奈之下,她只得把住在乡下的公婆叫到了安养。然而,丈夫连自己的父母也不相信。
“我承认两位和我的父母长得很像。可是,两位不是我的父母。真不知道大家干嘛都这样。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嗯?”
他掉过头去,不理会父母和妻子。对所有人而言,异常痛苦的时间缓慢地、极其缓慢地流逝而去。直到几个月后,他们才终于弄清楚他所经历的问题原因。他患上了一种名为“卡普格拉综合症”的特殊脑疾病。当头撞上地板时,产生了轻微的脑出血。而出血的部位,正好是右脑掌管有关亲密感的信息的地方。由于这一处出现了麻痹,他尤其对于从前关系亲密的人,在认知方面出现了混乱。医生如是说道:
“这不是疯了。如果是真的父母,理应感到的亲密感没有传来,所以他认为不可能是自己的父母。对太太也是一样。简单地说,就是
感觉身边亲近的人像陌生人一样。
本人也应该相当痛苦。”
他们没有离婚。当然是丈夫反对。和“假妻子”怎么离婚?他相信,总有一天,当“真妻子”回来,所有闹剧将会结束,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继续活在和谁也无法亲密起来的人生里,虽然觉得妻子是冒充的,却逐渐适应起来。仿佛被抓去北韩的渔夫们对新配偶附加上感情,就那样得过且过。
他决心移民。反正,在“周遭都被陌生人围绕”这点上,毫无差别。他们在法兰克福开了一家韩国餐厅。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现代医学仍没能治愈他的疾病,他与她依旧冷漠度日。
七年前,就在这家宾馆,我还对她说过这样的话:
“没必要太痛苦。就算没病,也有不少夫妻就跟陌生人似的。”
“你也那样?”
我一言未发。我不想亲口说出那种话。她抱住我。恨不得捏碎我浑身的骨头般,紧紧地抱着我。我知道她有多么渴望亲密,心想即便骨折,也要咬牙忍着。我们的床事和别人稍显不同。我们的床事,是舔舐、触摸、确认、爱抚、交换的过程。肌肤相亲,顾名思义,指肌肤间的亲密接触。我们长久地抱着,极久地撞击,更久地揉搓身体。我们彼此毫不怀疑。就在她去德国的三年后,在法兰克福的韩国餐厅偶遇时,我们一眼便认出了对方。我走出餐厅,在附近的公用电话亭里,往刚出来的那个地方打了电话。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我也没想到自己会当上餐厅老板娘。”
“我,明天准备去海德堡。你想和我一起去吗?”
“不行。我不能留下丈夫自己出去。”
她顽强地拒绝。
“我想你。”
“不要把偶然错当成命运。”
我独自去了海德堡。在市区闲逛,拍照,买明信片。喝下一杯浓浓的黑啤酒,吃了烤鸡腿。到了夜晚,回到预约的宾馆时,看到她站在前面。
“我很土吧?”
她问。那便是我们七年幽会的开始。我们就这样每年在同一家宾馆相遇。理所当然,她对丈夫怀有一股负罪感。也许有人会问,对认不出自己的丈夫,有什么好愧疚的?她的负罪感则带有一种复杂性。因为这一罪恶是无法得到宽恕的。即便她自我坦白,丈夫也会漠不关心。因为她不是真正的妻子。他会说:“我就知道会那样。你是冒充的嘛。我真正的老婆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来。”那么,如果认为便可以随意出轨的话,有这种想法的人想必并不了解人类这一复杂的存在。如今对她而言,交往其他男人只与自己的伦理有关。在举目无亲的陌生大地,如果想要守护自己,便需要某种愚昧的虔敬之心。然而,她的此种虔敬之心因我的出现而瓦解。她憎恨我。从我们第一次在海德堡相遇时起,直到那刻她对于自己的丈夫,对于围绕在身边的世界,一直坚守的那份精神上的正当性消失殆尽。说不定,对我的憎恨正是让她有了挺过一年又一年的力量。对孤独的人而言,需要此种感情上的支柱。我们的关系,由她那份复杂的负罪感与憎恨、对亲密感的希求,调和成一杯奇情杂陈的鸡尾酒。
然而,这一约会如今再也无法继续。我看到我的她,美丽动人的她站在我的房前。她从大衣口袋里抽出右手。用这只右手握住扶手,缓缓地转动起来。
“……在吗?”
她问。我也很好奇。我在吗?果真能说存在吗?我的肉身在那里,便能说“嗯,在,我在这儿”吗?啊,大凡所谓存在,究竟是什么?我明明在这儿,明明看着我爱的人,明明预感到了她即将感受到的痛苦,而我果真不在吗?
她茫然地站着。小心翼翼地走近,面对躺在床上的我,摇了摇我的肩。在她的摇晃下,我无力地动了起来。
“别闹了。”
想想,我好像很喜欢此种恶作剧。装死。每逢那时,她总是吓一大跳,而一旦真正遭遇,却似乎还不如那时震惊。
犹如爆破的大厦,她的身体瞬间坍塌。她正想用右手撑住梳妆台,却偏离开去。叮里咣当,发出一阵稍大的声响,她倒在了房间地板上。虽然比不上方才我的心脏发生的那阵剧烈的痉挛,她的心脏也猛烈地跳动起来。我能听见那声音。我高兴极了。这意味着她还活着。是啊。她活着。而这真是祝福吗?围绕在不信任自己的丈夫、每天登门的陌生食客、税务局职员之间度过的人生,是否真的值得祝福?我不确信。然而,此种苦恼如今已不属于我。我感到自己留在这个世上的时间所剩无几。我不知道自己怎会知晓。然而,这一点确切无疑。
她双膝跪地,爬着走出客房。好似金蝉脱壳,风衣留在了脚后。看上去她如同在这风衣里获得了重生。走到走廊的她,没有用德语,而是用韩语大喊起来:
“死,死,死人了。”
啊,我成了一般名词——“人”。她代替我的名字,管我叫“人”。前台胖胖的德国大婶,那个不可能听懂韩语的女佣气喘吁吁地爬上我们所在的楼层。我的她在哭泣。我从未见过如此悲痛的眼泪。虽然说起认不出自己的丈夫,谈到这一苦痛时,她会间或抽泣,但那是为自己的命运叫屈者的眼泪。她的哭泣不是发自口中,而是仿佛熟透的石榴绽裂开来,撕开肉身,迸发而出。如此地强烈。我没想到她的这一,原始的哀悼会这般甜蜜。我获得了慰藉。啊,亡者原本就是如此残忍的存在吗?如同吮吸生命的鲜血来获取满足的吸血鬼,此刻的我,对这一惨烈的哀悼,满意极了。
图为海德堡圣灵大教堂
远远地,救护车的警笛声强烈地传来。慢慢来,没什么可着急的。我想要告诉他们。是真的。没什么可急的。因为一切都已结束。即便如此,救护车仍顶着从树叶间洒落的,莲蓬头水柱般的阳光,在铺路石上一路颠簸。想想也是,死去的人自然应当赶紧送入亡者的世界。当然了。这是一件紧急的事情。某个人抓住脖颈,把我拉了起来。我冲破横穿豪普特街的鸽群,提心吊胆地躲开圣灵大教堂高耸的尖塔,向着无尽的高处飞升而去。我好似十二岁那年的水母,摇曳着透明之躯,浮游在虚空。我的眼眸清澈,肢体柔软,精神明净。在高空,我俯瞰古老的城市。羊羹般漆黑的内卡河上,铺洒着橙黄光泽的夕阳。适于思考人生的,便是这种地方。或许,来世我还会再来这里。永别了,亲爱的你。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shuimuasm.com/ssjj/77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