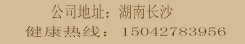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天敌 > 莫言小说中的创世纪神话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天敌 > 莫言小说中的创世纪神话

![]()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天敌 > 莫言小说中的创世纪神话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天敌 > 莫言小说中的创世纪神话
张学军孙俊杰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年第5期
学术评论
1神话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一种原初形式,存在于所有民族的文化之中。作为一种文学的传统,神话的潜影在讲求“天人合一”、“天道”与“人道”的中国古典文学中普遍存在,从六朝志怪、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普遍存在的神灵怪异,正是神话影响的结果。神话也渗透在张扬科学、理性、反传统、启蒙,强调面向人生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之中。鲁迅即认为,神话是小说之源与“本根”。鲁迅的《故事新编》、郭沫若的《女神》、沈从文充满神秘巫术气息的湘西世界,或采用神话的意象、原型,或以炫彩的笔墨直接记录民族历史中的神话传说,以此来喻示作家自己对生命、人性、历史和现实的体验和思索。有学者曾断言,20世纪又是一个神话辉煌的时代。文学创作者和理论家们也开始将目光转向远古神话、仪式、梦和幻想,“试图在理性的非理性之根中、意识的无意识之源中重新发掘救治现代痼疾的希望,寻求弥补技术统治与理性异化所造成的人性残缺和萎缩的良方。”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众多小说家面对社会现代化的飞速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精神和现实问题在文学创作中不约而同的一种趋向。
中国当代文学也出现了神话因素。年代中期的文化反思热潮中,许多寻根小说将写作触角伸向远古、荒僻、野蛮和闭塞之野,自然而然地涉及了神话这一贴近远古、荒僻之野的思维和文化形式,同时魔幻现实主义的巨大影响也使当代小说中的神话因素更为普遍,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刺猬歌》,姜戎的《狼图腾》,贾平凹的《废都》、《古堡》、《怀念狼》、《秦腔》,徐小斌的《羽蛇》等等。年,世界范围内兴起了神话重述的热潮,中国一些作家参与其中,产生了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李锐、蒋韵的《人间》、阿来的《格萨尔王》等作品,它们基于远古神话的骨骼,以当代人的理解和想象重构其血肉。神话因素的加入,不仅带来当代文学文体的各种新变,它对于想象的、虚幻的、非经验性、超现实的书写,对“现实主义”真实背后的探求,呈现出对现实、历史、人性的别样洞察。这也正符合世界潮流中对神话的认识,“从德国的浪漫主义者、柯勒律治、爱默生和尼采以来,这一术语所包含的新的观念逐渐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即‘神话’像诗一样,是一种真理,或者是一种相当于真理的东西,当然,这种真理并不与历史的真理或科学的真理相抗衡,而是对它们的补充。”在物欲膨胀、精神匮乏的时代背景下,在虚与实的对照中,也附带着寻找和构建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化意义。
莫言创造了自己文学上的地理——“高密东北乡”,他以充满野性而蓬勃的语言讲述着也建构着这一故乡的历史和当下,以飞腾的想象使之弥漫着神话的色彩。在这一方面,既显示了莫言小说与人类文化传统的相通,也与其他具神话色彩的小说一起汇聚为时代文化的投影。
2年底,莫言读到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正是福克纳的创作使莫言深有所悟,“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地胡说八道”,“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而且可以虚构地理”,遂有了“高密东北乡”的出现和建构。对“高密东北乡”这一“中国的缩影”,莫言也有意识地去追溯它的历史源头。对深受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思想影响的作家来说,追根溯源正是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在文学上的遗留。在莫言的作品中,最早具有“高密东北乡”创世纪意味的是短篇小说《秋水》。《秋水》追溯了“高密东北乡”的由来和创建,它以“我”这一后代视角讲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开创“高密东北乡”的壮举。“我爷爷”和“我奶奶”——一个下层男子和一个小姐之间跨越等级界线的恋爱,不容于社会常规,最终“杀死三个人,放起一把火”,两个人出逃到这一荒蛮之地,“成了高密东北乡最早的开拓者”。一场旬日不绝的大雨导致了洪水泛滥,在这样令人绝望的环境中,还有“我奶奶”分娩的痛苦。但《秋水》不仅仅是关于爷爷奶奶开拓与繁衍的故事,它还关联着其他的人物和事件。小说后半部分的叙述已经发生了转向,脱离了“爷爷”“奶奶”的主体。在洪水将他们所在的这一处小土山变成生命的避难所之后,有了不知从何处漂来的紫衣女人,也因她的出现,“我父亲”得以出生。同样还有了不知从何而来的黑衣男人与白衣盲女的故事,隐身于人物语言中的神枪手老七和紫衣女人的母亲,黑衣男人精准的枪法,白衣盲女的三弦琴与歌唱以及纠缠于紫衣女人与黑衣男人之间,黑衣男人、盲女和老七之间的恩怨等等。这些人物在小说中只是一种颜色的标志,相关的故事和矛盾冲突也仅仅是一闪现,都未被展开,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加入,使高密东北乡具有了多重的主题变奏,有了后来“消息慢慢传出去,神话般谈论着大涝洼里有一对年轻夫妻,男的黑,魁梧,女的白,标致,还有一个不白不黑的小子......陆续便有匪种寇族迁来,设庄立屯,自成一方世界”,也才会衍生出“鬼雨神风”的众多奇闻轶事,展示着内在的丰富和神奇。
“我爷爷”和“我奶奶”逃离原有社会对荒蛮之地开拓的主体故事类似于西方人类起源神话“失乐园”的中国式改版,其中充满带原型意味的意象和象征。小说中这样描绘了彼时“高密东北乡”的地理环境:“那时候,高密东北乡还是蛮荒之地,方圆数十里,一片大涝洼,荒草没膝,水汪子相连,棕兔子红狐狸,斑鸭子白鹭鸶,还有诸多不识名的动物充斥洼地,寻常难有人来。”荒蛮之地、各色动物,是中外创世神话中普遍的背景,它们给人幽远深邃的时空感,使创世的行为弥漫着神话色彩和魔幻气氛,也更具仪式性。近乎绝望的处境又加分娩的痛苦,在人与恶劣环境的对抗中,更衬托出创世者无畏的勇气毅力和创世的艰辛。动物是莫言所创建的“高密东北乡”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部分,在其作品中大量地存在,《秋水》中出现了各种鸟、鱼、昆虫和其他动物,色彩斑斓又生机勃勃,充满怪诞和跃动的力,给人以强烈的冲击,使人无法忽略它们的存在,也无法逃离它们的视野,既形成与人相对照的另一个世界,以野性自由的精神趋向为人类提供了自我的观照物,动物的自然神性也使小说弥漫着浓郁的魔幻气息。洪水袭来后在棚内穿梭般跑动与人争食的盈尺的饿鼠,月光中满山白的耀眼的野鸟,将树的枝杈压弯,使人“恍惚间觉得树上挂满了异果”等。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似乎也要被同化,动物性特征也渐渐凸显出来,原来剽悍的“我爷爷”“在阳光里眯起那两只鹰隼样的黑眼,下巴落在双手里,身体弯曲成饿鹰状”,奶奶的举手投足“似受伤的大鸟”。动物的人化和人的动物化倾向充分显示了动物作为“高密东北乡”这一荒蛮空间的主体地位。
洪水是神话中常见的模式和意象,它是远古的洪水灾害给人类心灵留下的集体无意识。《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洪水承载了人类的原罪意识,意味着惩罚和灾难,但又提供了社会秩序得以重新组合的契机,也增强了人类生存的本领和创造的智慧。鲁迅的《不周山》和《理水》即分别赞颂了女娲的宏伟创造和大禹治水无私为民的精神,王安忆的《小鲍庄》也正是由于洪水,洪水中作为仁义之子捞渣的死,使小鲍庄的人物都得到了救赎,困境由此得到合理的解决,小鲍庄重新建立起另一种平衡。《秋水》用四分之一多篇幅对滔天洪水极尽描写,在洪水中,“我爷爷”所能做的就是一面不断安慰处于分娩之痛的“奶奶”,一面不断走出窝棚查看水情,渲染了环境的险恶和绝望,也是因为漫天的洪水,使“我爷爷”所在的高地具有了诺亚方舟的意味,不仅动物泛滥,也引来了黑的紫的白的、活的死的各色的匪种寇族,形成了多向复杂的人物关系,才真正构筑起独立一方又野气纵横的新的世界。
与《秋水》几乎同时问世的《白狗秋千架》,把高密东北乡由《秋水》创世纪的传说,拉进了现实生活场景。它以莫言惯用的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呈现了农村少女暖的悲剧人生。美丽纯真的少女被偶然路过的军人尤其是蔡队长激发起对未来的美好梦想,这一梦想却被秋千架上的一次意外——一只眼睛的失明残忍地毁灭,嫁给哑巴后又一胎生下了三个哑巴儿子,繁重的农村劳动不幸的命运早已改变了暖的模样也磨砺了她的性格。当暖见到“我”之后,她最大的期望就是“我”能给她一个会说话的孩子,并勇敢地让白狗把“我”引到高粱地来。女主人公暖对生活不屈、坚忍、自尊而坦荡的形象散发着红高粱味道的“高密东北乡”气,这也正是莫言热衷塑造的故乡女性的某种精神共性。作为叙事者的“我”对暖曾有过青春的情怀,对暖的秋千架之殇也负有一定责任,并一直深怀负罪感。这是“我”离乡十年之后的第一次回乡,低沉而带忧郁的叙述语调正如七月末高密东北乡燠热难挨的天气,契合着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对故乡现状的失望、罪感的沉重和人生无奈的感伤。《白狗秋千架》第一次出现了“纯种”这一莫言小说所创造的带原型意味的概念。
在年前后,莫言还创作了一系列具有鲜明魔幻意味的小说,《白狗秋千架》《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大风》《爆炸》等等,甚至在小说中直接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魔幻意象进行模仿和借鉴。《白狗秋千架》对那条全身皆白、只黑了两只前爪、神色遥远荒凉的白狗的描绘即充满主观的体验和魔幻色彩,过去的故事以“我”的回忆或意识流的方式复活在当下的时空也是新时期现代小说中常见的时空结构方式。但总体上,无论过去的回忆还是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小说基本上采用主体化强烈的真实再现,现代艺术技巧融合在整体现实主义的书写中。此后“高密东北乡”成为莫言小说中的专用地理名称,所有的小说都被放在这个环境之下。莫言依恃着“高密东北乡”这一虚构想象的王国,在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尤其蒲松龄等为代表的古今中外文学传统以及山东高密民间文化的影响和浸淫中,飞扬起超拔的想象。《秋水》《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酒国》和《蛙》等等,共同建构起一个无限宽广的文化空间和“文学的王国”,使“高密东北乡”成为“中国的缩影”。
3年,莫言又创作了《马驹横穿沼泽》,同样是“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如果说,《秋水》是一篇创世传奇,那么《马驹横穿沼泽》的核心是一个人间男子和超自然女性(马驹变幻的美女)的恋情故事,则近于神话了。也因近于神话而自然呈现出更为浓郁的神秘和魔幻气息。
《马驹横穿沼泽》的核心是一个人兽交合创建家园的故事。一匹红色的小马驹和一个小男孩历尽艰辛横穿沼泽,在共同的磨难和相互扶持中,小马驹对男孩产生了爱慕之情,在得到了男孩永不提“马”字的承诺之后,幻化成一个美丽的姑娘与小男孩结为夫妇。他们终于来到遍地是没人深的野草、“人种没有一个”的地方。他们搭起了草棚,开荒种地,打猎逮鱼,养鸡养狗,生儿育女。多年以后,长大的儿女们竟有了悖逆人伦的行为,由男孩长成的男人一时愤怒违背了最初的誓言说出了“马”字,导致妻子化成马驹消逝,男子也因悔恨成为活死尸。可以看到,这一核心故事与《秋水》中“我爷爷”“我奶奶”创世的模式基本一致,具有越轨——惩罚的基本结构。他们同“我爷爷”“我奶奶”一样,有着苦难境遇中自然成长的真挚的爱情,但人兽之间的爱情同跨越阶层的爱情一样,显然也是悖逆社会常规的,只有在沓无人烟的荒蛮之地,他们才可能摆脱规范的禁锢,结为夫妇。这样的越轨已潜藏着惩罚的必至,只是《马驹横穿沼泽》中的惩罚已不再是自然的滔天洪水,更带有后世文明所赋予人类的伦理意识。它也给我们提供了其他带原型意味的意象,诸如沼泽、蹼膜、马驹等等,这些意象较荒蛮之地和洪水更具有莫言的独创性。而且这些意象不仅贯穿于《食草家族》的每一部分,也常出现于莫言其他小说中。这种跨文本之间的反复出现,使之承载了属于莫言的更为丰富的象征意义。
《马驹横穿沼泽》的叙述方式是很独特的。包围这一核心故事的是一代代人对它的讲述:黑色男人对生蹼小杂种的讲述——“我爷爷”对我的讲述——“我”对孙子的讲述,而“我爷爷”的故事又来自他的“爷爷”,用一句话来概括《马驹横穿沼泽》就是“我”给孙子讲“我爷爷”从“他爷爷”那听来又曾对我讲过的黑色男人给小杂种讲马驹横穿沼泽的故事的故事。在这样的叠加中,处于时间链条后面的每一层讲述都包含了前面讲述的有关信息,并加入自己的想象和描绘,而自我的感叹和怀想在这过程中也都化为神话的一部分。如在“我”对这个故事的讲述中,既有“我”现在对故事的认识,又有“孙子”听故事的反应和问话,以及“我”由当下情境触发不断想起的自己儿时听“爷爷”讲故事时的情境和情感反应。既有“我爷爷”讲故事时他的情态表现,又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黑色男人给小杂种讲这个故事时的氛围、环境以及他们各自的反应。有关黑色男人给小杂种讲故事的种种以及对故事的理解和处理,显然也来自“我爷爷”并经过了“我”进一步的补充和改造。在这样魔幻般的叙述中,红马驹和男孩创建高密东北乡的核心故事,距离讲述者越远,它自身在讲述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小。这既使马驹故事的本来意义趋于模糊和变形,也是对它的不断丰富。在一层层相互包含的讲述中,历史本身成为一则神话。
作为神话,人兽结合的核心故事本身即具有神秘、怪诞的色彩。《马驹横穿沼泽》又在整体上大量使用了象征暗示、隐喻怪诞、下意识心理、多角度叙述、时空顺序颠倒等等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多人称相互包含的讲述呈现了一个幻想与现实相结合的魔幻而深邃的历史时空。远古的历史不断在当下复活再现,又与现实融合在一起,现实在神话的笼罩下亦呈现着梦幻般的不真实感,真耶?幻耶?在其中,不仅仅人物——神秘的黑色男人,生蹼的小男孩——充满了神秘和怪诞,还充斥着其他各种怪诞的意象:连绵的红色的沼泽与沼泽地里如花如絮的烟瘴,苍狼的怪叫、男人的锐利的歌唱、绿色的或如游动的小蛇或跳动不安的火苗,火红色的油蚂蚱......这些感觉化的意象反复出现,强化了魔幻般的氛围。如同不同时空下怪诞意象的不断复现,历史似乎也在循环地演出。所有的讲述都是在三棵大柳树下,小杂种在这里等候黑色男人听其讲故事,爷爷在三棵柳下给我讲,“我”在三棵柳下给孙子讲;所有的讲述发生在同一的时间情境:傍晚,沼泽里升起团团烟雾,他们升起了一堆火;无论小杂种还是“我爷爷”、“我”、“孙子”,一代代人有着对“马驹为什么要过沼泽”重复的追问和对红马驹共同的怀想,男人的歌唱穿越了历史深长的隧道在每一次讲述中回荡,连油蚂蚱都从历史的深处一路走来:
“草地上......油蚂蚱蹦来蹦去,我稚嫩的皮肤被油蚂蚱弹打得生痛......我苍老枯槁的皮肤上站着一只油蚂蚱,火红鲜亮的颜色,油润有光泽,它如同玉石雕就,活脱脱一个宝贝儿,它脚上的吸盘弄得我皮痒痒,抬手擦掉了它......爷爷,蚂蚱碰得我肉痛,孙子哭哭咧咧地说着。我们到三棵柳下去吧,那里草少蚂蚱也少。
我被爷爷讲述的黑色男人吸引着,几乎见到了他的面容,头发蓬松着,恰如一股黑烟......爷爷打死了站在他胳膊上的油蚂蚱,领我到了三棵柳下。”
由现实到意识到想象,由视觉到感觉,由稚嫩到苍老,由孙子到爷爷到黑色男人,在这跳跃的碎片的粘贴中,时间似乎已经消失,莫言从容地引领着我们在现实、历史和神话的时空中自由飞翔。
从《秋水》、《白狗秋千架》到《马驹横穿沼泽》,对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莫言经历了从传奇——现实——神话推演的过程。在叙述方式上,它们都采用第一人称“我”讲述的方式,但因讲述层次的不同,三部作品的叙事结构本身正与内容上创世纪神话建构过程相一致,也正形象地呈现了历史和神话得以形成的过程。《秋水》是“我”讲述“我爷爷”“我奶奶”们创建“高密东北乡”的历史,这样不太遥远的时空,正是传奇得以诞生的土壤,在叙事的过程中,时空的距离和细节真实的悖论已经呈现了历史的虚构性和想象性,如对爷爷从洪水中拖上来的死尸的细腻描写,宛如在场般真实。《白狗秋千架》是“我”讲述“高密东北乡”现在的故事,是“我”之所历所见,强烈的现场感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马驹横穿沼泽》则通过几层的讲述向时空更深处勘探完成了神话的建构,每一次的讲述都是一次流传,也是一次改造和丰富。这是一个创世纪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神话形成和流传的故事,是文化和历史传承和丰富的过程。
4从《秋水》中“高密东北乡”的首次出现,继而《白狗秋千架》和《马驹横穿沼泽》,莫言何以一次次建构“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呢?由传奇、现实而神话,每一次的建构都将笔触更深地探入人类思维和文化的源头。联系它们所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应不难以对之作出解释。
《秋水》和《白狗秋千架》都发表于年,《马驹横穿沼泽》发表于年。年代中后期,正是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思潮兴起大行其道的时期,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思潮中,不仅产生了阿城的《棋王》(《上海文学》年第7期)、韩少功的《爸爸爸》(《人民文学》年第6期)、王安忆的《小鲍庄》(《中国作家》年第2期)等等大量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他非寻根作品也往往加入文化的因素。在寻根小说中,神话不仅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和思维方式使小说具有魔幻的色彩,又以其远离现代城市和现实乡村的另一种生存状貌和文化特征,映照着当下文化的缺失及其根源。寻根小说力图寻找民族的文化之根,将对文化的反思追溯到创世之初也是很自然的,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庄》。在《爸爸爸》所构建的鸡头寨,他们的生活中充满原始思维的神秘,占卜祭祀,迷了路是遇见了“岔路鬼”,要赶紧撒尿赶紧骂娘,蛇会被女人迷惑动情,丑陋猥琐的白痴丙崽因为只会说“爸爸爸”和“X妈妈”被人鄙视,也因为只会说这两句话又被认为具有隐秘神启的能力而成为“丙相公”、“丙仙”,被推到至高的神座受众人膜拜。这些使小说呈现着独特的美学风格,而落后、闭塞、停滞又充满血腥和杀戮的文化空间,自然具有文化审视和批判的意蕴。鸡头寨流传着祖先刑天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刑天生了优耐,优耐有了火牛,火牛有了府方,府方有了姜凉,姜凉正是他们的祖先,五支奶和六支祖在凤凰的引导下来到此地创建了鸡头寨,使它成为闭塞、神秘又年代模糊的所在。祖先的英勇与后人的愚昧又顽强地生存,都有着或正或反的联系。《小鲍庄》的开端也是小鲍庄的创世神话。小鲍庄的祖上因治水不力,深为愧悔,“于是带了妻子儿女,到了鲍家坝下最洼的地点安家落户,以此赎罪。从此便在这里繁衍开了,成了一个几百口子的庄子。”小鲍庄人的生活和命运、捞渣的“仁义”之举都被统摄在洪水泛滥先人治水的神话氛围之下,使小说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有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反思,也衍生出“罪”与救赎有关命运的思索。
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秋水》和《马驹横穿沼泽》所讲述的“高密东北乡”创世纪传说和神话便不可能是孤立的,自然容易被纳入寻根的视野,从而带有文化反思的意蕴。在文化空间上,它们同大多寻根小说一样,都属于近乎封闭或边缘的荒原之地,人物所携带和开创的文化即成为这一空间的文化传统。在人物形象上,不仅“我爷爷”、“我奶奶”、有着“乌黑的撸子枪”的紫衣女人、“神枪手”黑衣男人、“黑巴鱼样”“瘦得像一道黑烟”的黑色男人等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和怪诞气息,《秋水》中还有无比纯真似绝世而独立的白衣盲女,也正是白衣盲女所唱的儿歌被“我爷爷”教给“我”从而被传唱下去。《马驹横穿沼泽》有无名无姓也无家可归的手上生蹼的小杂种,小杂种的蹼膜则关联着高密东北乡起源的古老神话传说,成为人类梦魇的一部分。这些怪异的人物在年代中后期的文坛也正如莫言发表于年的《透明的红萝卜》中主人公黑孩一样,不仅是小说所述年代的黑孩,“还应该是‘年文学’的黑孩”,是年后的寻根、先锋小说中大量存在的“身心障碍”、“哑巴”、“聋子”、“痴呆者”人物谱系中的一员,“都无非是对当代文学那个以英雄为主体的所谓‘正常人世界’的合法性的篡改。”
神话是人类文明的源头,莫言重述一个神话作为高密东北乡创世纪的源头,也是很自然的。《马驹横穿沼泽》后被收入长篇小说《食草家族》,成为它的一部分。而通过《食草家族》的整体,也能够更充分地看到《马驹横穿沼泽》的寻根意义,它成为家族的、民族的历史源头,也是文化和精神的源头。《食草家族》以梦来命名每一部分,它构建了家族的人物谱系,大老爷、大老妈、二姑奶奶、小老舅舅、“我”、儿子等等,也书写了家族内部的爱恨情仇。家族内部人员之间的关系都是冷漠的,充满了欺骗、监视和倾轧,围绕性与生存的争斗和复仇几乎是人物命运的核心元素,由之产生了血腥、残酷的伦理悲剧和家族灾难。《红蝗》中大老爷为了与红衣服的小媳妇偷情将其公爹毒杀,又和四老爷因小媳妇大打出手,小媳妇也被杀害。大老爷设计抓住了大老妈与锔锅匠的奸情,让刺槐刺瞎了锔锅匠的一只眼,并借机将大老妈休掉。五十年前的伦理纷争又与五十年后的黑纱裙女人、教授等相互映衬和对照。《玫瑰玫瑰香气扑鼻》中生蹼的小老舅舅名义上的父亲黄胡子,因妻子被支队长霸占,利用支队长和高司令赛马之机将支队长杀害以复仇。《二姑随后就到》中二姑因生了蹼膜成为家族中的一个梦魇。因曾被家人遗弃,二姑不仅亲手射杀了曾遗弃自己的父亲,攻打过家族的院垒,要向建议遗弃自己的大爷爷大奶奶复仇。多年以后,她派自己的两个儿子天和地重回家族,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清洗了家族中的长辈。还有直接以《复仇记》命名的一部分,生蹼的挛生兄弟一直背负着名义上的父亲临死前的嘱托,要寻老阮报仇,而老阮正极可能是他们的亲生父亲。莫言将《马驹横穿沼泽》作为第六梦,放在此书的最后部分,正是追溯了食草家族的创世源头以及伦理悲剧的根源。男孩与红马驹在困境中结合创建“高密东北乡”,已经注定了人类悲剧的宿命。它一方面体现着人类最为原始的欲望——生存与生殖,就如同人类自然产生的对于红马驹的怀想,“世世代代的男子汉们,总是在感情的高峰上,情不自禁地呼唤着:ma!ma!ma!”,它是美好而真诚情感的象征,所以对红马驹的描绘那么美丽而多情。另一方面,创造与破坏往往共生,苦难中热烈的爱情与日常生活情感倦怠的荒诞,高密东北乡开天辟地的壮举诞生了手脚生蹼的子孙。正是人与马的结合,使其后代身上几乎命定地永恒地具有了兽性的遗留,它潜藏着膨胀为野蛮、残忍与伦理越界的可能性。在现代视域中被定义为发展、进步、完善的对立面,而在人类历史上,欲望不断扩张确如红色的沼泽,衍生了无数的罪恶和争斗。这些在人身上的铭记即是蹼膜。《食草家族》的每一部分几乎都存在手脚生蹼的人物,《玫瑰玫瑰香气扑鼻》中的小老舅舅,《生蹼的祖先们》神秘的老姑奶奶和梅老师、“我”、霞霞等等,《复仇记》中近乎痴傻的挛生兄弟,《二姑随后就到》中只出现在人们讲述中的二姑,以及《马驹横穿沼泽》中的小杂种等。蹼膜成为食草家族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核心意象,是其无法摆脱的一部分命运,带有了“原罪”的意味。众多的伦理悲剧都与之相关。而蹼膜正是作为文化本原和人类祖先的男孩与红马化成的女孩结合的结果。
5除了在时代文化场域中具有文化寻根的意义,这几部作品同样应放入莫言对“高密东北乡”这一王国的整体建构中来考察。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与韩少功的鸡头寨、王安忆的小鲍庄明显不同。它既是现实实有的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又是想象虚构的文化地理。作为故乡,它在中国的文学场域中从来不仅是生活之所,更是精神家园,是生活意义和生命意义的源头,是作家构建乌托邦的凭依。莫言对故乡的每一次书写,都成为一次寻根筑梦之旅。“高密东北乡”自从首次出现在《秋水》之后,莫言的大部分作品都可以说是围绕它的一种讲述,是对它历史和现实的不断丰富。在这一点上相类于鲁迅的未庄、沈从文的湘西,更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的约克纳巴塔法世界像仿佛。创世纪神话和传说便是“高密东北乡”的文化之源,是形塑“高密东北乡”这一王国的人民性格、心理和精神的文化根源。
作为“创世纪”,《秋水》几乎衍生了高密东北乡所有的精神元素。爷爷奶奶为了爱情杀人放火,未曾展开的老七、黑衣男人和白衣盲女之间的纠葛,在生存的形式上,他们具有沈从文“湘西世界”中人性原初的真,又将湘西和谐的美演化为粗粝和躁动的浓烈。《白狗秋千架》中的暖已经具有这样的精神元素。他们上演着匪种寇族之间的争斗、仇恨和凶杀。这种争斗更多来自生命的本能欲望,不同于革命的阶级对抗,是身体狂野而自然的欲望呈现。莫言对这样的欲望采取的都是搁置道德、历史等主流评判标准的民间立场和态度。在这样的空间里又萌生着神秘而超越此在的思维:坐着釉彩大瓮被黑衣人从水上推来的白衣盲女,似梦幻中人超脱于外界而独立,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她无法理解人们的问话,从哪里来和叫什么名字都是一个谜.而当周围的人们都陷在惊恐、争斗、仇恨中时,只有盲女在自足的世界里笑着呈现着幸福的光晕。这种天真、超然、无识,使她具有浓郁的象征的意味。她所哼唱的儿歌犹如人世的谶语,小说结尾“我爷爷”教给我的一首儿歌表明它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中被承传下去。“高密东北乡”作为乌托邦与恶托邦的所在,还有着不受常规社会伦理道德的制约,人物近乎自治的精神的自由。此后,《红高粱家族》中的“我爷爷”和“我奶奶”们又将这些演绎到生命的极致,野合、杀人放火、爱恨情仇、土匪之间的斗争,这些在民间的价值观念、抗日战争的背景、现代性等多重语境中产生了多重的含义。《檀香刑》中眉娘与钱丁之间本能的热烈的吸引,孙丙的酷刑在猫腔的盛大演出中成为一场悲喜剧色调的精神狂欢同样如此。带魔幻意味的神秘思维也正是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民间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也正是这些精神元素使“高密东北乡”成为一个“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成为“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的一个完整的世界。而对祖辈精神的书写,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暗含了《白狗秋千架》已经提及的“种的退化”的命题。
《马驹横穿沼泽》具有更为复杂的情感倾向,他既表现了爱情神话故事的神奇迷人,又极力渲染了它使人战栗的恐惧。奔跑不停的红马,美丽的姑娘,男孩与红马驹的爱情故事是使人迷恋的,被一代代人讲述流传和向往。但在流传的过程中,它使人迷恋的除了红马驹外,还笼罩着一代代人深深的恐惧。小说在讲述这个爱情神话故事时,极力渲染了一个阴暗而使人恐惧的氛围:来自坟墓去向坟墓的黑色男人和无家可归的生蹼小杂种携带着神秘和怪诞,死寂的沼泽突然发出的怪响如虎啸如狼嗥,黑色男人冷酷的脸和冰冷的语言,他的莫名其妙的歌唱在黑夜的死寂中伴着苍狼的怪叫,突然爆发的哨子虫的尖利鸣叫令人心惊胆颤。莫言用大量阴暗、怪诞的意象,讲述了红马驹故事的现实氛围和人物感觉的可怖。在其中,听黑色男人讲述马驹横穿沼泽的故事的小杂种是恐惧的,在小杂种的眼里和意识中充满了怪诞吓人的意象:“他把一只粉红色的蚂蚁诱到草棍上,让它沿着草棍往前爬,如同面临万丈深渊,蚂蚁搔首踌躇。他感到了恐怖。一只黑色的脚,宛若一只独立的怪物,漫过他的肩头伸到他的面前。他闻到脚上的味道:幽幽野菊香。蚂蚁跳上他的过分突出的脚趾,很快地往上爬,爬过脚背,爬上脚踝,看不见了就扭脖子回头:黑瘦的男人青白分明的眼睛盯着他,坚硬的唇边漾着青苔状的微笑,嘴里是两排钢铁牙齿......”而对小杂种和黑色男人等怪诞意象的渲染,使同样听“爷爷”讲红马驹的“我”和听“我”讲红马驹的孙子也都充满了恐惧。一个原本美丽(虽然带着悲剧意味)的神话故事在流传中诞生了恐惧,成为一代代人对恐惧与迷恋的情感传递。
这样混杂的情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莫言自己的儿时体验,大爷爷讲似真似幻的鬼怪故事也让当时的莫言着迷又心惊,“越怕越想听,越听越不敢往家走”。莫言对这些表现出格外的迷恋,在他的很多小说中都能读到这样的神灵怪异故事。如《战友重逢》中钱英豪讲述父亲曾讲过的故事:胶河大王大白鳝能化成白衣书生到岸上作孽,两个下河洗衣服的大闺女被河水淹死变成了一对小蛤蟆。《我们的七叔》中七叔对狐狸精故事的渲染,都使听者感到心惊。这也是人类普遍的生命体验,对一切未知和神秘事物的好奇与恐惧,也是神话诞生的基础。《马驹横穿沼泽》将既迷恋又恐惧的情感和爱与生存、欲望与蹼膜、黑色男人对苍狼的呼唤,与“兄妹交媾啊人口不昌——手脚生蹼啊人驴同房——遇皮中兴遇羊再亡——再亡再兴仰仗苍狼”的警示连接在一起,具有了莫言的主体色彩,充满对生存哲学、对历史发展的超常性思考,也体现了他对历史发展、对人性善恶的评判态度。红马化为美丽的女子与男孩在危难中结合开创了高密东北乡,这一迷人的故事,具有一个人类历史发展中更为根本性的问题:伦理的悖论和含混。对此,莫言悬置了历史发展、道德惯例的评判尺度。他看到了现实生活游离于政治、历史、道德等现代价值标准之外的混沌,人性的复杂,人类发展中残酷与非理性存在的必然性。正因如此,那对因悖逆社会规范相爱的生蹼的青年男女被施以火刑烧死,在《生蹼的祖先们》中被描写的凄美又壮丽;大老妈因偷情被休脖子上挂着情人的大鞋骑在毛驴上的形象如一个英雄(《红蝗》);皮团长对生蹼男孩的阉割在历史正义背后是它的残酷和血腥(《生蹼的祖先们》)。这是一个原始而混沌的人类生存状态,是民间生存的本相,正如在《生蹼的祖先们》里“我”的最后感悟:“人都是不彻底的。人与兽之间藕断丝连。生与死之间藕断丝连。爱与恨之间藕断丝连。人在无数的对立两极之间犹豫徘徊。如果彻底了,便没有了人。”在迷恋与恐惧并生的混杂中,它拒绝了既定世界政治的、道德的、审美的明确规范和秩序。这也是莫言作为老百姓来写作的一贯立场。
感谢张学军老师授权本号发布!
这是一个有温度的甲氧沙林搽剂北京中科白癜风专治白癜风转载请注明:http://www.shuimuasm.com/sszz/8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