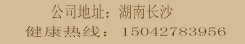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天敌 > 在限制的刀锋上舞蹈莫言访谈下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天敌 > 在限制的刀锋上舞蹈莫言访谈下

![]()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天敌 > 在限制的刀锋上舞蹈莫言访谈下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天敌 > 在限制的刀锋上舞蹈莫言访谈下
写打油诗算是慕古人之雅兴
张清华:再说说您的诗吧,早年写的那些打油诗,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诙谐的、调侃和日常性的讲述中,有的甚至不无禅意。所谓“打油”其实是诙谐精神的体现,因此日常性和禅意是两个必备的元素;作为它之间的张力的,即是诙谐精神。通过诙谐实现其美感,通过禅意实现其境界,通过日常性完成其现实感和有效性。您的打油诗我认为总体上是具有这些元素的。
从打油诗到最近写的这些自由诗,我以为也有一个风格的一致性,就是诙谐。诙谐一方面是有自我调侃,有社会讽喻,同时也是在艺术上的一种现代性追求的体现,所以是您的这些诗的灵魂和生命所在。庄严的抒情不是说不能存在,但是单纯的和庄严的、浪漫主义式的抒情,在现今可能缺乏现代性的意味,或者说和现实之间的及物性的对接是不够的。但在您的诗里面,便通过诙谐而使诗意更加松驰,更加具有了现代意味,具有了讽喻性和自嘲的特点。另外还有一个,便是有很多“超现实”的因素,像《在高速公路遇见外星人》《雨中漫步的猛虎》《飞翔》等,包括您与帕慕克的对话中,里面也有超现实的东西,就是你的书像鸽子一样飞出去了,等等。总之这是我的个人感受,您在诗歌写作当中抱有哪些意图或者是追求,也跟读者说一说。
莫 言:首先是打油诗。写打油诗的时候没想到要发表,而我的打油诗多半是跟书法(准确说是用毛笔写字)联系到一起的,拿着毛笔写字,你老抄唐诗宋词也没意思,一边写一边想。诙谐是民间口头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民间讲故事的人都能够把一个哪怕很沉痛的事情讲得很诙谐,会把故事幽默化,这是一种处理故事的民间方式,也是民间故事能够引人入胜的一个特征。把苦难幽默化,这是生活现实,是我的乡亲们的生活态度,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的社会环境中,诙谐、幽默也是存在的。算了,这些话就不说了。我写打油诗就是为让朋友觉得好玩,或者自得其乐,笔下也就很随便、很松驰,没想到发表,不去想那么多。但偶尔我的打油诗会被传到网上,带来很大的麻烦,会被做一些违背你原意的、甚至政治化的解读,我感到很无奈。诗无达诂,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脖子后边留胡子——随辫(便)吧。
写打油诗的历史跟我练习书法的历史差不多同时的,截止到目前大概也写了几百首,有的有点意思,大多数是没什么意思。因为诗歌说到底更像是一个“抄来抄去的艺术”,很多句子你看都是似曾相识,描写风景的、描写离别的、描写情感的,都已被唐人、宋人写的烂熟了,当代人无论怎么写都难以达到古人那种水准,所以至少对我来讲,所谓旧体的诗,不论七言的还是五言的,只能走诙谐的、黑色幽默的、自我调侃的这个路线。当代确实也有成功的范例,就是聂绀弩,他的诗应该是当代典范,他不是那种故做深沉、洒狗血的老干体,凑够七言四句或者七言八句就斗胆冠以七绝、七律,我从来都不敢把自己这种诗冠以律诗之名,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甚至连打油诗我都不敢说,打油诗都不够,顶多算“打酱油诗”或者是“地沟油诗”,过几天我准备下点功夫,学学律诗。
词,这个形式我就更不行了。第一,读的量少,要写的话就是照葫芦画瓢,多数人写《沁园春》,都以毛泽东的《长沙》和《雪》为蓝本,然后在其意韵的基础上写自己的东西。所谓“填词”,便是硬往里“填”,“凑”出来的,跟古人把形式烂熟于心中不一样,古人是写出来的,或者是脱口而出的,我们现在是硬凑的,怎么可能好?清末况周颐《蕙风词话》里说,句子很好,意思很好,但是不合律就很痛苦,怎么办?只能是不断的换来换去。有时候因为一个字改一句,改一句最后通篇全都改,有时候改来改去初稿一个字没剩,全都变了,但是在改的过程中没准又灵感突发。
所以我想,到了清朝,写词已不可能像宋人那样容易了。前人的杰作,就是后人的枷锁。我们当代人如果要用这种陈旧的形式写作,更不容易了。山东人——尤其我们高密人,是四声不分的,四声不分就区别不了平仄,这就很困难。还有入声字,那就更加困难。前一段我老家的那个小石桥坏掉了,这小石桥是明嘉靖年间修建,距今已经多年,也是《红高粱》的外景地,在那打过仗,打过日本人。坏掉之后,市里面拨了几万块钱重修。修桥的时候从桥墩下面起出十来根老枣木,这枣木当年作为木桩支撑桥梁的时候,是经过防腐处理的,什么手段不知道,据说是“油炸”过的。在水下浸泡多年,已变成黑色,像钢铁一样,在那扔着没人要,我就要了两根。枣木本身就很硬,用了切割大理石的钢锯才把它锯开,切开后我做了十几副镇纸,想写几个对联刻上去。我写了“支桥长奏洪波曲,伏案漫观汉唐书。”对联最基本的要求,上联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仄声,下联最后一个字是平声。‘曲’仄,‘书’平,符合要求,但第六个字对不上。从字面上看很工整,但平仄有毛病。真正写出一幅好的对联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推敲。有的词很好,但是平仄不对,这也是戴着镣铐跳舞。
话说回来,这是中国的传统。中国过去考验一个人有没有才华,就是能不能立刻对上一个对子,我们见到很多所谓的天才都是童年时期能出口妙对,师傅出一个天他对一个地,师傅出大海他对高山……现在这些东西虽然已经很陈旧了,但我们这种酸臭文人,偶尔还会有这么一点情结,有这么一种慕古人之雅兴。
张清华:有没有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出一本打油集或新诗集?
莫 言:我刚才说为什么要写新诗,目的就是要借此读新诗。坦率地说,原来很多新诗看两行我就感觉晕头转向,什么意思啊?后来我自己拿起笔来,我说写两首新诗试一试,通过自己写,我再读你们写的诗,便发现能读懂了,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所以我写新诗,是为了读别人的诗。要成为一个好的欣赏者,最好首先成为一个创作者,一个写过小说的人读小说,肯定比从来没写过小说的人读的时候感受更丰富,写剧本、写诗歌都是如此。尤其是写诗,写现代诗,只有你写过,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读出什么叫好来。打油诗集,或者新诗集,都要先积累到足够的数量,然后精选一下,让你们这些专家看看,如果有点价值就出书,没有价值就算了。
忘掉一切,想怎么写怎么写
张清华:再问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问题。通常说来,一个作家的创作也是有曲线的,某种意义上说,会有高峰,有山丘,也有低谷,是一个不平衡的、但走势上又必定会有一个大致的曲线。有的作家在年轻时代即写出了代表作,后来的作品虽然从手艺上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但作品本身的影响力却呈递减趋势,也就是说,一个作家一生的创作好像也是有一种宿命。您对自己未来的创作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判或者期待?我个人觉得你过去的写作有几个高点或峰值,比如说年轻时代无疑是《红高粱家族》,90年代当然是《丰乳肥臀》,世纪之交是一个成熟期,作品的手艺炉火纯青,《檀香刑》肯定也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像《生死疲劳》是手艺最纯熟也是最炫技的一部作品,但这几部之间也并不是完全等量齐观的。在得奖以后有,有几年是沉寂的,而现在看来又在恢复,您自己预感还会写出体量比较大、艺术创造力能够和以前媲美甚至超过以前的作品,还有没有这样的决心和抱负?
莫 言:决心还是有(笑),但是能不能用才华证明这个决心?这真是自己都不知道。前五年,尤其是前两三年,天天处在精神和身体的疲惫之中,现在慢慢在恢复写作的能力。标志是我感觉到笔下有东西写了,不像有一段时间拿起笔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很焦虑,现在感觉到还能写,但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这不去管它了,我想也不要过多去考虑。前两年我之所以轻易不敢出手,还是有压力,大家预期太高了,东西一出来肯定被人笑话,与其那样还不如不写。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忘掉过去的一切,爱怎么着怎么着,想怎么写怎么写,写的好是它,写的不好还是它,反正我就这么写了,这样也许更好。带一个很高的预期来写作,铆着劲要写一部《红楼梦》,要写一部伟大作品,往往适得其反,那些扬言要写伟大作品的人从来没写出来伟大作品,那些熟知伟大作品配方的人,也从来没写出过伟大作品,只有那些写的时候随意而写——管它如何,好是它、坏是它,一百万读者是它,两个读者也是它——这种全然放松的以自己的审美判断为依据的创作,才可能写出不错的作品来。所以我现在努力调整到忘掉一切,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这么一种状态。已经六十多岁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发挥一点余热,首先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小说艺术的追求,感觉到我对小说的探索还没有到鸣锣收兵的时候,感觉还能够再往前冲一冲。另外,也是希望用自己的写作来报答那些对我满怀期待的读者朋友们。
小说结构艺术上,最满意《酒国》
张清华:如果给自己的作品排个队,比如说从最好开始的依次来排个队,您怎么排?
莫 言:这个真是没法排。从我早期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跟《红高粱》哪个好我没法判断,《透明的红萝卜》跟《爆炸》哪个好也没法判断,《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怀抱鲜花的女人》,包括《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牛》,这些中篇都算是在一个水准上的,而且是风格各异的。长篇《红高粱家族》严格说是中篇组合,它作为一部长篇缺少构思的一贯性,只是后来组合而成。
张清华:或许它正是一个意外的创造。
莫 言:意外的是最终变成了一个长篇,基本上算是符合长篇的一些要求,因为一段段的发表,结果变成了我所有小说中最独特的一种时空处理,空间、时间给切得很乱,而且现代跟过去完全畅通无阻。我刚得知这两天有一个尼加拉瓜的南美作家的书马上出版,他说读过我的《红高粱家族》,他对我的处理时间和空间的技术很欣赏。
张清华:我在年写过一篇《〈红高粱家族〉与当代长篇小说的文体变革》,是从当代文学史、长篇小说文体演变史的角度,谈这部作品的价值的,当然文章发的时间已很晚,但我是很早以前就思考和谈过这些问题。
莫 言:这个时空处理的手段,实际上也许很简单。你说我受了西方影响也可以,你说我受了二人转和民间戏曲影响可能更准确。
张清华:我主要是从“简单进步论的终结”这个角度谈它的贡献,它终结了社会学和进步论尺度中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结构的基本模型,促动了当代长篇小说的文体变革的进程。但总体上我还是认为《丰乳肥臀》是最伟大的作品。这是我从世纪之交以来一贯的一个看法。
莫 言:《丰乳肥臀》的人文意义是最丰富的,不管怎么说,还是写出了上官金童这样的在当代文学里面未曾出现过的形象,现在不是有成群结队的“巨婴”吗,我想他们的祖先也许是上官金童,写了这么一个男人。也写了上官鲁氏这样一个母亲,这也许就是《丰乳肥臀》这本书的贡献,但你非要把上官金童的恋乳症,说成精神变态、性变态也不是不可以,也可以这样解释,但是我想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之意不在乳,可能上官金童恋乳也暗示出人类最基本的弱点,所以从人文学的意义上来讲,这本书可能是有些价值的。
但是也像你刚才讲的那样,对结构艺术,我自己最满意《酒国》,《酒国》这个小说的结构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可谓独树一帜,年那时候谁写过这样的小说?包括之前的《十三步》,《十三步》的结构是对人称实验的一种全方位的拓展,还有《欢乐》这部六万字基本没分段的作品,对第二人称“你”的叙事实验,也是在当时不多见的。
有生之年再写一部长篇,
或希望还能回到年轻时候的写作状态
张清华:《欢乐》写了多长时间?
莫 言:两个星期。当时我的中篇都是一个星期,《红高粱》一个星期,《天堂蒜薹之歌》28天,所以我几十年来的创作时间累计起来不到三年,其他时候都在干嘛?如果写三十年呢?
张清华:其他时间是在准备。
莫 言:只能这样安慰自己。我现在说哪怕三十年里面写了十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成果?作品多出三倍来才对。
张清华:这是“创作”和“写作”的差别。写作是一种工作,每天都是一种工作状态,早上起来吃过早饭,弄杯茶往这一端,电脑前一坐,就开始写作。这是职业化的、常态的一种工作性质的写作;对您来说,可能就是漫长的等待和孕育,然后突然出现,进入疯狂的创作。
莫 言:但愿还能回到年轻时候写《红高粱家族》,写奶奶去世时那种迷幻的状态,写《欢乐》里面齐文栋喷洒农药的那种感觉。
张清华:这样说吧,您骨子里也还是个诗人,没有诗人一样的创造激情和灵感式的突如其来,可能您的作品不会像现在这样充满异样和“魅性”的感觉。
莫 言:在中国因为“中篇”的命名法,埋没了很多作品,法国人的一部小说也就是五六万字。我的《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牛》《欢乐》《筑路》等,如果把它们略微扩展,就是长篇。一个“中篇”,通常不在大家的视野之内,也很难将其作为一本书单独出版。像《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牛》的幽默感,我认为在我的小说里是独树一帜的,但都没有办法像长篇那样得到读者重视。
张清华:《牛》我在当时看时,确实觉得太震撼,它对于一个牲畜的生命也是写得那样生动,纤毫毕现,摄人心魄。
莫 言:一位旧日的朋友,说他的太太读《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笑得在床上打滚。如果我把它写成一部小长篇,八、九万字,单独成书,保持风格的统一性,不就使我的风格更丰富了吗?《欢乐》也是一样,如果我把它再加上两万字,不就是一部用第二人称写成的很有风格的长篇吗?这样,影响肯定比中篇大。
张清华:确实“中篇小说”这种体制和认知,可能埋没了一些本来有可能非常重要的作品。不过这也许就是一部作品的“命运”罢。我觉得都不用改了,因为所有的作品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莫 言:这确实不能改,再改没有意思了。它作为一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不能再改了,还可以再写。短篇小说我还是要写,我还有几部写了一半的话剧,已经构思了很多年的,但不知道何时能完成。
张清华:不断有说法,言之凿凿说您在写长篇,最近有写长篇的计划吗?
莫 言:长篇放到最后吧。我也很遗憾,大家对我的长篇充满期待,很多人问过:写长篇了吗?我说没有,写剧本呢。大家都认为长篇是衡量一个作家最高的标准,这实际上也不对,长篇短篇不是标准,契诃夫一辈子也没怎么写长篇,也很好。汪曾祺先生也没写长篇,当然还有鲁迅。写剧本,曹禺先生一辈子也就那么几个剧本,也是大师。
张清华:有传世之作足矣。
莫 言:但是长篇还是要写一个,在我有生之年再写一部长篇。
张清华:我预感可能不止是一部。
莫 言:要写的素材,五部恐怕也够了,但不知道能不能有力量写完。
过去三十年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作品
张清华:最后一个问题:我一直有这么一种感觉,用黑格尔的话讲叫“时代精神”或者叫风云际会。我感觉中国文学真正风云际会的时代可能已成为历史,比如说从年新潮文学的风起云涌,到年先锋小说的次第登台,上世纪八十年代实现了文学的变革,九十年代实现了文学的收获,世纪之交以来是一个变奏和多元的时期,但是总体上我感觉,从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说,可能一个“黄金时代”甚至“白银时代”都已结束了,眼下或者以后,不过是“黑铁时代”或者“塑料时代”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是个人中心主义的经验方式,可能把自己的生命经验投射到历史当中,对历史会产生一种偏差性的认识。就您来说,以您的体会,当代文学过去的三十多年,您亲身经历的三十多年,是怎么评价的?对眼下文学的场域氛围,这种新的历史境遇,是怎么看的?未来又有什么期许和判断?
莫 言:我认为现在低估了过去三十年的文学成就。我是不同意当代文学这三十年不如现代文学那三十年的说法,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还是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作品。现在大家谁说了也不算,再过三十年回头看,也许那时候看的更清楚。
至于当下和今后的写作,这个不敢妄言。我没有充足的阅读量,我对当下的这些作品,除了几本重要的刊物偶尔翻一下,缺乏广泛的阅读。任何一种对一个时期文学的判断,首先要建立在广泛阅读、起码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品读一遍的基础之上,你没读几部作品,凭感觉妄下断言是不靠谱的,也是最不负责任的。
至于未来,我相信一句话,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作家,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文学,现在不能拿我们的作品跟曹雪芹的《红楼梦》来比较,这不在一个比较的语境里面,只能拿我们这三十年的文学跟国外同时代的文学来比较,放在一个世界文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不能把现在我们的生活指数跟唐朝的人比较,你比什么?唐玄宗也没用上手机,杨贵妃也没戴过手表,还是放在一个世界范围来比较我们的三十年,我认为我们不比别的国家的作家写的差。
像我们这批50年代出生,包括60年代出生写苦难的作家,如果描写当下的生活,肯定写不过“90后”“00后”,人家是接地气的,我们是不接地气的。要写的人物也还是我们周围的人,你不能全方位的了解这个社会各个层面、各个年龄段的人的状况,你要写出一部具有广泛涵盖性的、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生活的本质的作品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还是寄希望于年轻人,他们应该写。我们还是写一些我们的边角剩料,写一些素材仓库里面所残留的那点东西。
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经典出现
张清华:本来刚才是最后一个问题,但我又想到一个问题也很重要:这三十年来文学的繁荣或兴盛,跟大的历史转换可能有关系。我们作为一个原始的农业国家,一个农业民族,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乡村社会处于解体的过程当中,乡村经验已经碎片化。像您作品中所表现的那些自在的、完整的、原始的、并被投射上浪漫色彩的、民俗意味的乡村经验系统,以后可能就不会再存在了。作为您这一代作家自然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使命——在我看来是写出了乡村社会或者农业文明的“最后的挽歌”。这是从比较宏观的角度给出的认识,今后文学必然会有一个谁也难以扭转和控制的一个巨大变革,即书写乡村经验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作家不得不去书写城市经验或者是现代生活经验。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转换?
莫 言:这个也没有办法,好像进入了工业社会,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样,文学尤其是小说越来越类型化,类型越来越多,过去好像就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股潮流,现在各种各样的,玄幻的、科幻的、神魔的、职场的、情场的、历史的,所谓的农业题材、工业题材已经是不存在了,因为社会现实在发生着快速变化。也老是有人问我怎么看当下的乡土文学,我说当下依然还是有乡土文学,但是已经是变化的乡土,你不能还是用鲁迅年代《故乡》的乡土,也不能用我的《透明的红萝卜》的乡土来比较当下的乡土,所以每个作家也都在与时俱进,因为每个作家都不可能停留在原地。
总之,每个作家还是在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出现像托尔斯泰那样包罗万象,变成时代一面镜子的作家的机率越来越低。文学受到商业化强有力的牵制,它在影像化、电视剧化,很多写作明显能看到受到电视剧巨大的诱惑,也就是商业的诱惑,这个也无可非议。我们也不要指望一个时代所有的作家都写出经典来,我们只是希望在一个时代留下几部经典,我相信曹雪芹的时代也有很多人在写作,在托尔斯泰时代、在巴尔扎克时代,作家都是成群结队,但是最终大浪淘沙,留下的就那么多。否则人类也不堪其负,那么多作品怎么读?所以,每个时代能够留下的几部被大家公认的经典,是这一代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幸运地落在某几个作家的头上而已。你不能说托尔斯泰伟大,就把托尔斯泰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否定掉,他们在共同地努力,共同地烘托。巨大的力量托起一个高原,高原托起一个喜马拉雅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托起一个珠穆朗玛峰,没有高原,没有山脉,它也挺不了那么高。唐朝成群结队的诗人托起了李白和杜甫,没有广阔的诗的高原,高峰挺在哪里?所以我一点都不悲观,我相信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经典出现。
最后我补充两句:一,如其说经典是“捧”出来的,还不如说经典是“骂”出来的,当然,最根本的,经典还是写出来的。二,要想让所有人都说你好,那是不可能的,你小心翼翼地生怕得罪了人,但也许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就制造了一个一辈子不放过你的仇人。
本文首刊于《小说评论》年第2期,原文约2万字,拆分为上下两部分,5月25日推送了访谈(上),至此推送完毕。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uimuasm.com/sszz/414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