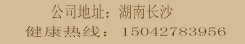我烧了一杯热水放在我的桌子上,我捂住了它像捂住生命之泉一样。它的热量在我掌心的纹路间传递,热气从杯口上方不断地溢出,这又多么像生命的流逝啊。近来常有一个问题盘踞在我的心头,我的生命是否真实?也许我在乔鲁斯镇的所闻所见都不过是一场幻影,也许我现在也压根不在莫斯科。现实有时候就跟梦境一样,既荒诞又虚幻。当我们对这个理性世界产生怀疑的时候,当第一个为什么诞生的时候更多的为什么就会接踵而来,紧接着“荒谬”这一个词便会在你的脑海里生根发芽,你会意识到理性世界的存在是非理性的。
我问你们,为什么世界上存在名为“巧合”的东西,为什么偏偏是你像垃圾一样被倒到现世这个巨大的臭烘烘的垃圾场里?我们找不到答案,可理性告诉我们我们得有一个答案,古代挪威人望见乌云中攒动的闪电便惊呼是托尔抡着铁锤在云中驰骋,古希腊人无法理解天空为何如此高远便创造出泰坦阿特拉斯用双肩支撑苍天,他们笃信的一切在如今看来是多么荒谬,相信我我的弟兄们,我们所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许多东西也会像我们否定过去人一样被未来人否定。幸运的是,当下的我们还可以谱写属于这个时代的浪漫神话。
在我升入哲学系那年,乔鲁斯镇来了一批不速之客——吉普赛人。
这个消息是萨诺奇在餐桌上告诉我的,自从萨诺奇有了两个奇丑无比的儿子之后就将我彻底遗忘在学校旁边的房子里,并不是我有意贬低这两个孩子,而是他们的长相实在像是上帝造人时用尽了泥巴而后随手捡了两块石头拼凑成的。
那时萨诺奇为他的烟斗填充着烟草同我讲道“最近曼纽河边上来了一群老鼠。”
我蹙起了眉头问萨诺奇“老鼠?”
“吉普赛人。”萨诺奇嘬起了烟斗“鬼知道这群旋转水晶球的屎壳郎为什么到乔鲁斯镇来。离他们远些,除了下三滥的把戏,他们什么也不会。”
为了避免争论我点了头默许了萨诺奇的话,可他人越是禁止的东西我便越是想要去探个究竟,正是萨诺奇的这番话像佳肴的香味一样勾起了我饥肠辘辘好奇心,吉普赛人也正在那时像个摇晃的摆锤敲击着我内心的大钟荡起阵阵余音。
我在哲学系认识的第一个人名叫福斯莱特,他长得像极了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尤其是他那头不羁的头发,他出生贫寒因此造就了他编造故事的本事,他用子虚乌有的事情来装饰自己比如说他常说自己的父亲曾在国王倒台那年受到国王召见,原先他也可以成为一个贵族诸如此类的无稽言论,因此他被我们戏称为“讲故事的人”。
这位“讲故事的人”显然同我一样对吉普赛人充满了兴趣,他约了我翘课一道前往吉普赛人那儿。
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我跟福斯莱特前往曼纽河畔的场景,我们从早上出发于中午才穿过那片死气沉沉的市区,我像一个沉默的旅人穿行过一片黑森林而福斯莱特更像一只在枝干上横跳的聒噪乌鸦。
走出市区时天空变得像一床沾了水的厚实棉被,福斯莱特走在边上问我“你知道这群吉普赛人是如何出现在乔鲁斯镇的吗?”
我如实讲道“我不知道。”
这位讲故事的人一下子跳到了我的面前“我可是乔鲁斯镇第一个碰见吉普赛人的人。”
“那你讲讲你是如何碰见他们的。”针对福斯莱特这号人物最好的办法不是让他们沉默而是拿下堵住他们嘴巴的塞子,让他们像开闸的水库一样一吐为快更何况我们总把福斯莱特的故事当做一种消遣。
“该从哪里说起呢?三个月前,得从三个月前说起!”福斯莱特停顿了一会儿,就像一个作家在冥思构建情节似的“那时候我们不是正好结束升业考吗?我就开始思忖如此漫长的假期我该如何度过,你知道的依我的性子可不愿意在家里度过那么长的时间,这会把我逼疯掉的,于是我常跑到商业区那一块儿,我期待一种邂逅。你知道的,有点艺术细胞的人总喜欢做一些看似荒唐又毫无意义的事情,我经历了许多天的失败,我连一件有趣的事儿都没有碰上,渐渐地我对这种小说故事中才会出现的情节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但这不意味着我不再尝试了,你知道的,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赌徒,他们暗暗发誓再赌一次再赌一次!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态期许着遇见什么人,没想到还真的被我撞上的,塞布尔,你认识艺术系的贝蒂娜吗?”
福斯莱特望向我,我蹙起了眉头,我怎么会不认识贝蒂娜?在福斯莱特提到贝蒂娜的一瞬间我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就好像一个陌生人突然提到了我珍藏已久的宝物一样,我装作与贝蒂娜并不熟悉的样子询问福斯莱特“我听说过她,怎么了?”
“那可真是个美人,不过,我要说的可不是她,而是她的朋友珍妮,她长得是如此的……唉,塞布尔,你知道的,我可不擅长这些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招数,所以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她……噢!鸽子!你知道的,塞布尔,鸽子总是象征着希望与爱,珍妮就像只鸽子一样洁白无瑕,啊,至少第一眼看见她我是这么以为的。为了同她们攀上话,我制造了许多巧合,你知道的,爱情可不会平白无故出现,机会往往是需要自己创造的,必须得让她们觉得‘噢,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我在她们的必经之路上徘徊跟她们拐入同一家商铺,一共同她们相遇了五次,这可累坏我了,每一次相遇我都会装腔作势地打上一声招呼,这可没有你想的那样轻松,你必须像个绅士一样优雅。当然,这对我来说并非什么难事,你知道的,塞布尔,我离贵族头衔只差一步之遥。你知道的,当我们陷入巧合的旋涡中的时候,我们就得像一个投机商人一样抓住时机,你知道的,这世上看似有许多机会,但这许多机会就像一阵有去无回的风不会再吹拂你第二次,机会出现的时候必须牢牢抓住它!必须趁热打铁!我询问贝蒂娜与珍妮是否要共进晚餐,这是一次冒险,正是这次冒险让我有理由相信连贝蒂娜都爱上了我,可遗憾的是我的心里只有珍妮,只有那只白鸽,贝蒂娜对我说‘我很想同您共进晚餐,可遗憾的是晚上还有一场宴会,很抱歉。’而珍妮同意了我的邀约!幸亏贝蒂娜没有接受,我身上的钱压根不够三个人吃的,你知道的塞布尔,现代人都喜欢把钱放在银行这都成了一种时髦,当然我也不例外,放在身上的现钱自然没多少,后来……后来怎么着来着……”福斯莱特像个不知停歇的抽水泵喋喋不休讲了那么多显然是有些累了,他低着头在脑海里组织着他的语言,不一会儿倏地抬起了头来“对!珍妮答应了我,你知道的塞布尔,如果不是两情相悦,哪个女孩子会答应一个陌生男子的邀约,我跟珍妮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漫长的晚上,那晚可花光了我所有的钱,但正如……正如莎士比亚说的‘任何时候为爱情付出的一切都不会白白浪费’……”
很显然,这句不知出自谁之口的名言并不是莎士比亚说的,“爱情是一种疯”倒是出自莎士比亚之口。他还在呶呶不休的往下讲我却没什么心思再听下去了,他讲到这儿依然没有吉普赛人半个影子,至于他说的贝蒂娜爱上了他这就更是无稽之谈了,他的口头禅“你知道的”还在我的耳际乍响就像城市中突如其来的尖锐杂音,我承认我有些后悔让他讲述他是如何碰到吉普赛人的故事了。我同福斯莱特已经走到了曼纽河边上,四周没有风,河水静的出奇只是平缓的向前流动,这对平时湍急无比的曼纽河来说简直算个奇迹,从这儿走到曼纽桥附近还有着些许距离。
“你还在听吗?塞布尔?你怎么心不在焉的?”福斯莱特打断了我的思索。
“我在听,你接着讲吧。”我像一个上课犯困的学生又强打起精神听福斯莱克讲下去。
“她欺骗了我,欺骗了我这个可怜人!你知道的,水母绝大部分是由水组成的,可爱情呢,绝大部分是由金钱组成的,珍妮意识到了我是个穷光蛋!你知道的,我并不是一个穷鬼,只是我的钱都放在了银行,我存的钱金额巨大及时去取也需要周转许多时日。你知道的,一个人一旦丧失了希望他什么事儿也做得出来,于是我做了件蠢事儿,啊!十足的蠢事!我去找萨克借了高利贷……”
福斯莱特提到的这个人好像一根实木棒子狠狠地击中了我的后脑勺,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我打断了这个小丑的故事“萨克?”
福斯莱特愣了一会儿“是的,萨克。”
这个蠢货显然还不了解我跟萨克之间的过节,我再三确认“是以前文学系的那个萨克吗?”
“嗳呀,我差点忘了,你和他可是同学呀,这就好办了,你替我说说情说不定我都不用还贷款了。”
“噷!我劝你千万别这么做。”对于这个小丑似的角色我越发鄙夷。
“好吧,我对你们的故事并不上心,那笔钱对我来说只是一笔小钱,我还得上!请接着听我讲故事吧,你知道的塞布尔,我这个人总是心软,即使对于珍妮这样的女人也不例外,我用这笔钱买了一对钻石耳坠想让她回心转意,可她说什么‘这又是从哪儿捡来的玻璃玩意儿’你知道的塞布尔,只有男人的自尊才会像玻璃一样禁不起女人轻轻一推。我大光其火,愤懑无比,当她说出那句话的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这辈子都不会再去找她了,当晚我就带着那对钻石耳坠去了‘托克大道’噢,对不起,我不该叫它的原名,你也许听过他的另一个名字‘风俗大道’你知道的,这些地方对我来说算不上陌生,我随即走向一家最大的娱乐会所,我敢肯定你没见过这场面,我看见每个人的胸膛里都有一团被欲望点燃的火在熊熊燃烧着,这场景简直像是地狱中才会出现的,赌的赌、嫖的嫖,如果地狱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我倒还是有些向往的,嘿嘿。”福斯莱特发出了黄鼠狼般的笑声,他接着讲了下去“塞布尔,你吃过禁果吗?我在去那儿之前可从来没有品尝过,你知道的我是一个老实人,这事我只对你说,你可千万不能对别人讲起,我下定决心离开珍妮就像一根火柴狠狠划过火柴盒,我的欲望就这样一瞬间被点燃了,啊,真是愚蠢极了,实在卑琐实在卑琐,塞布尔,你可别因为这件事而瞧不起我。我将那对钻石耳坠丢在了老鸨眼前,那老鸨老得像一块满是褶皱的千层饼,她拿出了放大镜仔细看了看真像一个上了年纪的鉴宝专家,你知道的鉴宝专家往往是这样做的,噢,对了,还有她无名指上的那颗硕大的红宝石戒指可真是耀眼……”
“红宝石戒指”这几个字像牵引球一样抛出去又被我接了回来,我打断了福斯莱特的话“那女人是不是瘦瘦高高的,是不是叫做玛利亚?”
这会儿轮到福斯莱特疑惑了“你怎么知道?”
紧接着福斯莱特舒展了面部的表情“我明白了,你我是同道中人,你一定也去过!是不是?”
我没有回答,巧合的子弹打在了我的胸膛上令我不知所措同时我在等待着他继续讲下去。
“好吧,我原本还想炫耀似的给你讲述了一下云雨之欢,如同花蕊般的姑娘,啊,她们的胸脯是多么美妙啊。那该讲什么呢?该讲什么来着?”
这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丑,一面说着自己卑琐一面又把自己做的蠢事像一位骑士拔出自己的宝剑一样亮出来炫耀。我不想从他的嘴里听到任何我熟悉的人的名字,于是我提示到“吉普赛人。”
“噢,对了对了,我要讲的是吉普赛人,我扯得太远了,嘿嘿。我离开了那家妓院的时候偶大概是凌晨四点,我还死皮赖脸讨了一瓶威士忌,毕竟那一对耳坠价格不菲。你知道的塞布尔,夜晚总是会酝酿忧郁,因为珍妮的缘故,这忧郁成了一片沙漠,而解渴的清泉就被我握在手上,当然,我说的是威士忌。我离开的时候,乔鲁斯镇正笼罩在晨雾中,整个乔鲁斯镇就像一个盖着被子在酣睡的婴儿,你知道的塞布尔,某些时刻我是拥有一个诗人的潜质的。那片大雾和我脑袋里的酒精混在了一起,我看不清脚下的路,我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就好像雅各在睡梦中登天梯一样,不知不觉间我竟走到了曼纽桥附近,连我自己都讶异我竟走了如此一段距离,而后奇怪的事情便发生了。我突然听到了‘丁零当啷’的声响,起先我还以为是我喝多了,我朝着曼纽桥上望去,只听见马蹄声与物件碰撞声愈来愈近,一团橘黄色的亮光在浓雾中忽隐忽现,你知道的塞布尔,死神驾着马车来索命大抵也是这个场景,我自然被吓得不轻,慌乱地朝后边退去好几步,等到马车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才望到了马儿身后的大篷,大概是没有死神会驾着篷车来索命的,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通过马车上那盏煤油灯,看见了马车夫黝黑的肤色,你知道的塞布尔,这类人几乎都长一个样,这些奇怪的民族几乎都长一个样。第二天我才听到了消息,乔鲁斯镇来了一批吉普赛人。瞧见了吧,塞布尔,我可是乔鲁斯镇第一个撞见吉普赛人的人,这就好比罗伯特吃下第一个西红柿!”
在福斯莱特讲完的档口曼纽桥的轮廓在我眼前出现了,我所行走的这一岸满是黄色破碎的砂砾而另一岸却布满着苍翠葳蕤的大树,福斯莱特显然也望见了曼纽桥开始手舞足蹈起来“瞧啊,塞布尔!就是那座桥,吉普赛人就是穿过那座桥来的!加快脚步!我们马上就要见到吉普赛人了!”
那时的天空还未暗下去,像干涸的土地似的龟裂状的云仍在空中久滞不散,云层远远高于地面丝毫没有落雨的征兆,依然没有起风静的出奇,能听到的就只有我跟福斯莱特走过砂砾时发出的沙沙声响。吉普赛人的篷车在曼纽桥不远处,我跟福斯莱特并没有靠近那些吉普赛人,只敢像垂涎羔羊又害怕牧人似的野狼一样远远地望着,他们并没有像我想象中一样扎起帐篷,拢共有三辆颜色迥异大小不一的篷车,这三辆篷车似乎就是他们的栖身之所“塞布尔,这场景像不像梵高的那副画……叫什么……叫什么来着……”
“《吉普赛人篷车的扎营》。”我提示到。
“啊!对极了,你知道的,我这个人记性总是不太好。你瞧啊塞布尔,他们好像在跳舞,嘿,那个女孩是不是在看我们?”
有一个吉普赛男人蹲坐在地上拉着提琴,他周边的吉普赛人正跟着音律跳着弗拉明戈舞,福斯莱特所说的那个女孩正坐在一辆最小颜色也最为丰富的篷车上,双腿悬于地面像荡秋千似的摇晃着,吉普赛女性的衣着大多比较艳丽,那女孩穿着一条鲜红的裙子,裙摆的褶子处还绣着花纹,而后我才注意到她的脸,这是一张鹅蛋脸,微微蜷曲的黑发散在两侧不做任何整理,眼睛大得出奇就像在脸上镶嵌了两颗刚被水润泽过的黑葡萄似的,正如福斯莱特说的那样她正饶有兴趣地望着我们,她的鼻子倒是小巧的多以致于成了她脸上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器官,薄薄的嘴唇微微向上撇着现出一种戏谑嘲弄的冷笑,顺带一提她白得想一块奶油蛋糕全然不似吉普赛男人一样显出一种被太阳折磨得黝黑的病态肤色,但她的笑容让我极为不舒服似乎在对我和福斯莱特打什么坏主意似的,这时我又想起了萨诺奇的告诫便对福斯莱特讲道“既然已经看到了吉普赛人,我们就离开这儿吧。”
福斯莱特对我的劝阻不以为然“怎么了,塞布尔,你还怕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把你吃了去?你知道的塞布尔,这样观察吉普赛人的机会……”
“噢——诶——”福斯莱特的话还没有说完便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打断了,提琴声戛然而止,跳弗拉明戈舞的吉普赛人也停下了脚步纷纷望向我们这儿,这件意料之外的事情让我一时间不知所措两颊也瞬时间涨得通红,福斯莱特却像跟旧朋友打招呼那样高挥着手臂并对我说道“那女孩好像在招手示意我们过去。”不等我回话,福斯莱特已经朝着吉普赛人的方向前进了好几步“塞布尔,你再不来我可就一个人过去啦!”
我拗不过福斯莱特,也朝着吉普赛人的方向走去。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shuimuasm.com/ssjj/62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