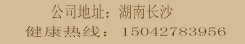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种类 > 残雪在国外的文学地位比莫言要牛得多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种类 > 残雪在国外的文学地位比莫言要牛得多

![]()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种类 > 残雪在国外的文学地位比莫言要牛得多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种类 > 残雪在国外的文学地位比莫言要牛得多
女作家残雪,本名邓小华,年5月30日生于湖南长沙。父母是三四十年代的中共党员,解放后在报社工作,父亲曾任新湖南报社社长,年父母双双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残雪从小由外祖母抚养,这位老人心地善良,但有些神经质,有一些怪异的生活习惯(如生编故事、半夜赶鬼、以唾沫代药替孩子们搽伤痛等),对残雪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残雪从小敏感、瘦弱、神经气质,短跑成绩和倔强执拗在学校都很有名。
她小学毕业后恰逢文化大革命爆发,便失学在家。年进一家街道工厂工作,做过铣工、装配工、车工。当过赤脚医生、工人,开过裁缝店。年结婚,丈夫是回城知青,在乡下自学成木匠。年残雪退出街道工厂,与丈夫一起开起了裁缝店。残雪自小喜欢文学,追求精神自由。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超过六十万字。
残雪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有三最
截至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残雪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有三最,作品被翻译得最多,作品入选外国高校教材最多,拥有为数众多的专门研究她的机构。
日本河出书房新社、春秋文艺出版社,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霍特出版社,意大利理论出版社,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中国蓝出版社,德国鲁尔大学出版社等10余家知名出版社,都出版过残雪的作品。
残雪的小说早已成为美国哈佛、康乃尔、哥伦比亚等大学及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日本大学、日本国学院的文学教材(在这一点上,莫言远不如残雪),她是中国唯一被收入美国大学教材的作家,也是中国唯一有作品入选日本河出书房新社“世界文学经典文库”的作家,其作品被美国和日本等国多次收入世界优秀小说选集
如同《红楼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解决了无数读书人的就业问题,许多国家也成立了专门研究残雪的机构(这点上,莫言也只能自叹弗如),如日本的“残雪研究会”,年就出版了《残雪研究》杂志。
年日本《读卖新闻》推介残雪的书,把她的头像与昆德拉、略萨(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并列在一个画面。
然而,这位当代中国最受世界瞩目的女作家,似乎永远游离在主流视野之外,正如她梦魇般的小说总是在诉说一种内心的孤寂。
残雪以其极度个人化的风格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似乎从上世纪80年代,她初出茅庐以《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等实验性作品震惊文学界的那一刻开始,她就没有怎么变过。齐耳的短发,刘海盖住了额头,还有一副略有些大的眼镜,永远是残雪个人形象的标志。
残雪奇特的文学语言和她所构筑的陌生世界一度让中国文学界争论不休。残雪似乎是活在梦中的。这是一些怎样的梦?她说:“从儿时起,我在大多数的梦境里都‘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小时候不懂得延长自己的好梦的技巧,只知道要逃避噩梦。如果老虎在后面追,我就要往悬崖上跑,跑到了就闭眼往下一跳,以便及时梦醒。”只是她并不承认她的小说和梦境之间的直接关系:“好久之后,我才慢慢知道,我的梦境同一般人的确有些不同,也许从一开始,我就隐藏着把梦境变成现实的野心。”
残雪执拗地描写噩梦和白日梦,与她的童年经验有着隐秘的联系。残雪的父亲曾任《新湖南报》(今《湖南日报》)社长,母亲也在报社工作。年反右风暴来袭时,父亲作为“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头目被打倒,之后,在“文革”浩劫中,父母再次遭劫。虽然残雪的小说从来不正面涉及政治问题,但那些寓言般的故事何尝不是在影射那段岁月?她的大弟在“文革”中的意外死亡让她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面对死亡。那个恐怖的下午,她没敢去看他的尸体。大弟在浏阳河里被漩涡卷进了取沙的农民弄出的沙坑里……残雪还时常在自己的梦中见到他。现实残酷的人生比任何一部梦魇般的小说都更像梦魇本身。恐惧埋藏在她的内心,以至于20多年来,残雪描写着这些让读者不安的故事从未改变。
残血自称典型的小市民
十一二岁时,看到别人挑担子,残雪心生羡慕,“蠢蠢欲动”。她之所以很愿意吃苦,是盼望自己在吃苦中变得强大。
就这么一个“很不怎样”的人,她的小说,现已成为哈佛大学、东京中央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的文学教材,但是,她从未上过大学,甚至连中学都没上过。约20年前,有某文学院要她去念书,说可颁给她硕士研究生文凭,她不去。“我去干吗?我要照顾儿子。”———尽管面对已是化学留美博士后的儿子,她给“母亲”一角的评分只有“70”。
残雪说自己是个生命力顽强的人———无论现实的困境,还是精神的困境,她总能突围。她自称“从小就有苦行僧的倾向”。“愿意吃苦,更盼望自己在吃苦中看到长进,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
十一二岁时,看到别人挑担子,残雪心生羡慕,“蠢蠢欲动”。家里不让,她就拿家里的煤折子去买煤。体重50多斤的她,用两竹箩筐挑了50斤煤回家。13岁时,便已挑得动70斤,而她那时体重才60斤。
三十岁开始写小说之前,她在街道工厂做过铣工、装配工、车工,还在街道做过赤脚医生;中学没念过的她,靠自学做了初三英语代课老师。
“我买不起收音机,别人给我一个巴掌大的半导体,一个茶杯口大的唱片装置,我跟着蚊子一样的‘唧唧唧唧’的声音学‘林格风’。在语言上,我没什么天赋,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坐得住而已。何况我和哥哥邓晓芒都遗传了酷爱哲学的爸爸的‘逻辑’。我能抓住句子的内在结构。所有东西都能自学,英文当然也可以。”当时,残雪已经自学了家里的部分哲学书、所有文学书以及所有能借到手边的文学书。“我搞得学生齐声朗读,校长还表扬我。”
年,已为人母的残雪,和丈夫就着家里“老缝纫机”开了家缝纫店,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做起了“个体户”。“我把家里的旧衣服拆开,再缝上。学得很快,大概三个月就开始接衣服做了。”
在残雪四十一二岁时,有过半年以上的时间,她觉得自己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后来就改易其辙,转攻文学评论。“读完卡夫卡就读博尔赫斯,读完博尔赫斯就读但丁,读完但丁再读浮士德……英文的读一遍,中文的读一遍。反反复复,一下子进去了,突然发现自己可以写评论了。创作是反省自己,评论同样是反省自己,只不过是通过别人提供的镜子而已。”等6本关于西方文学经典的评论专著出炉,残雪创作上的“瓶颈”也早已成为过眼云烟。
残雪自称同世俗的世界有着很深的计较,作品多在“计较”间诞生。而她长期处于交流的饥渴之中。年,此前从未想过当作家、顶多写点日记的残雪,因为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小说,结果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伏在缝纫机上搞起创作来。年,残雪的小说处女作《黄泥街》发表。“发表很困难。找大杂志,走了一圈,也没人接受,最后丁玲搞的一个《中国》杂志,要创新,要找一些年轻的、比较好的作品,这才把小说七转八转转到那儿。”
没想到残雪的写法,引起了海外文学研究者的注意。“年,日本、美国那边就开始介绍我了。”年,残雪的小说单行本《黄泥街》在台湾率先问世。“国内的出版社不大敢出,怕卖不出去。”
从处女作《黄泥街》到即将问世的新长篇《边疆》、自传《艺术与童年》,残雪坚持写着一种“矛盾”。“从小我就是个矛盾体,既孤独又不孤独,同这世俗的世界有着很深的计较。我同世俗的矛盾,是永恒的,是一种从迷惑、痛苦、徘徊到冷静、坚定的争斗过程。我的作品大部分描写的就是这个矛盾、这个过程。”
小时候的残雪,动不动就较真,常常同人决裂,而自己的行为举止又并非无可挑剔。对她而言,最大的快乐就是同自己喜欢的伙伴一起玩耍,“可我又动不动与他们闹翻,闹翻了又难以和好”,她就长期处于交流的饥渴之中。
她的青年时代,大部分日子都是在人际关系的焦虑中度过。“我也曾反省过自己,企图扭曲自己的个性,挽回一些败局。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成为了社会所不容的人。”后来成了作家,又一次卷进社会生活的乱漩涡,又一次为社会所不容。
残雪一边做着世俗的“我”,一边鄙视着。“同世俗中人的明争暗斗越频繁,自我反省就越深入,越有力度。”现在,残雪对世俗中的那些事和人,有着无穷的兴趣和斩不断的牵挂。“我永远是‘他们’之中的,但我在‘他们’当中又很难受、很压抑,对自己的行为也很鄙视。现在,尽管我探索的问题非常艰深,尽管我的所有小说都可以归结到人的本质或抽象的人性上去,我的故事和叙说依然带有浓郁的社会底层的气味。这,恐怕永远都改不了。这是我生命的基地,我的什么东西都是从这里起飞的。”
“所谓才能,说到底,不就是将人性中的那些本能坚持到底吗?很多人都是有才能的,可是能正常发挥的人却是那么少。”
有作家称,当下中国内地文学界,对残雪基本上持两种态度:一种是不予评价,绕道而行;另一种是围绕她的各种“传说”,比如说,因为崇敬卡夫卡,他们夫妇俩在家里的一切事务都是用爬行来完成的。对文学界关于自己的声音,残雪不是特别在乎,她在乎读者的声音。“哪天遇上一两个,就会高兴得不得了。”
虽然心怀出名的愿望,残雪还是坚持“要以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去出名,去卖钱。只依靠作品说话。人抵挡不了物质的诱惑,便放弃了自己的本性,也放弃了天赋的认识权利。”新作《边疆》,她说如果只有一两个读者喜欢也没什么。“你要觉得什么都不错,觉得内心所有的矛盾都已化解,就不用来读这部作品了。我的书,是写给那些善于自我分析、喜欢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谋求掌握自身命运的人读的。”
残雪从来就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属于未来的。有人说:“正如人们在几十年之后才知道了四十年代有个张爱玲一样,再过几十年,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我们这个时代有个作家叫残雪,只不过那时说这话的人已是我们的孙子辈了。”对此,残雪深以为然。现在,一个既定的事实是,每隔十来年,残雪便重新成为一个话题,被文学圈议论一下。让残雪欣慰的是,“在年之前,我总共只出过两本书。但现在,平均每年都有五六本书在国内外出版。”自处女作发表至今,残雪已有多万字作品,被美国和日本文学界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最具创造性的作家之一。“所谓才能,说到底,不就是将人性中的那些本能坚持到底吗?很多人都是有才能的,可是能正常发挥的人却是那么少。”
王蒙、王安忆、格非、阿城等一批当代文坛名家在她的书中成为反面教材,“我不喜欢文坛的那种风气”
残雪没再走出过自家院子———因为“家传”的风湿。“兄弟姐妹都有风湿。也许是我的职业,我的风湿反应为过敏,夏天都要穿两件衣服。不然要耽误我创作。”
更执著于精神的东西,也是残雪的家传。在她的回忆里,父亲“不是超时代的天才,只是一个爱思索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不仅有信仰,还有一整套贯通在生活中的逻辑。这套逻辑支撑着他,使他在最困难的年月里头也没有垮掉。似乎每个单位都要将自己单位的牛鬼蛇神抓起来拷打,然后关起来。我每天惴惴地观察父亲,但看不出什么异样。他照旧每天看报、看书,对社会做冷静的反思,做他该做的事。”有一天11点多,有辆大卡车停在街上,下来好多人。父亲才放下书本,对我们说抓我的人来了。
因为一本《残雪文学观》,文坛引发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震撼———王蒙、王安忆、格非、阿城等一批当代文坛名家在书中成为反面教材,被残雪逐一批判。她说我不喜欢文坛的那种风气。唱赞歌这么些年,完全没有不同的意见。对指名道姓要承担的风险,残雪称没想过。我与他们没什么交往,不会掺杂个人因素,是就事论事。除非我不说话,要说话就只能这么说。假如因为怕得罪人就不说话,等于我就不存在。
牧野赞赏
人赞赏
北京白癜风手术费用北京哪个医院可彻底治愈白癜风转载请注明:http://www.shuimuasm.com/ssjj/29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