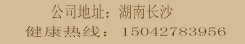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繁衍 > 心灵胎记与文学超越莫言散文的故乡意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繁衍 > 心灵胎记与文学超越莫言散文的故乡意

![]()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繁衍 > 心灵胎记与文学超越莫言散文的故乡意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繁衍 > 心灵胎记与文学超越莫言散文的故乡意
作者简介:
张洪波,女,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韩传喜,男,东北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要:
莫言散文中关于故乡的描写,形成了其独特的“故乡意象”,而“饥饿”与“匮乏”是这一意象的核心内质,如同生长于作家心灵的“胎记”,始终贯穿于其文学创作,被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呈不同姿态,反复纳入写作视野、取材范围与表现范畴,构成了莫言绝大多数作品的审美特质,亦成为探求莫言创作历程,观照与研究其文学创作独特性的最佳视角之一。
关键词:莫言;故乡意象;散文;艺术传达
与动辄长篇巨制、言丰意厚的小说创作相比,莫言的散文创作更近于简截短取、直言平述的随性写作。创作感言、旅游感受、生活感触……在其散文写作中皆有表现,然其中意蕴最为丰厚且富表现力的内容,还是其对于“故乡”的回忆与追述。故乡的山川风物、草木鱼虫、父母亲朋、师长同学……随着岁月的雕琢,刻写在莫言厚重的故乡记忆中,形成了其散文乃至贯通于整个文学创作中的“故乡意象”。而这些所谓“故乡意象”,已成为其文学王国的核心与灵魂,并因其独特的审美特质,成为观照与研究莫言文学创作的最佳视角之一。从其文风独特的散文作品出发,我们可以溯流探源,一探莫言本源性的“故乡经验”与其创作的密切关联,更好地认知与把握作家文学创作的独特性与普遍规律。
一、心灵胎记:“饥饿”与“匮乏”
莫言散文所涉题材范围,较之小说,似乎宽泛了许多,而其中最富生活质感与表现张力的,当属关于童年记忆和故乡生活的叙写。生长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方乡村的莫言,经历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古怪而狂热的时期”,“一方面是物质极度贫乏,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几乎可以说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另一方面却是人民有高度的政治热情,饥饿的人民勒紧腰带跟着共产党进行共产主义实验”。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代中艰难存活与磨练成长的莫言,人生最初与最强烈、最深刻的记忆,几乎都与人类生存的本能相关:作为生命个体对食物的本能需求及求之不得的极度折磨,与作为社会个体对情感的本能渴求及被冷漠置之的内在痛苦,浓缩为其散文乃至小说中“饥饿”与“匮乏”两种核心体验,共同合成为莫言早年生存困境的典型图景,并为其人生与创作打上了终生难褪的心灵胎记。
“饥饿”曾是那个特定年代一个民族的集体生理体验与共同心理记忆。对于莫言而言,“从我有记忆力起,就一直饥肠辘辘”。而食物的极度缺乏和难以下咽带来的,除了生理上的痛苦之外,还有生命上的严重威胁。“那时死人特别多,每年春天都有几十个人被饿死。”童年的莫言,便时时目睹并经历着这种似已成为日常的悲剧事件,因而,当饥饿与死亡联袂而至时,原本应该单纯快乐的童年,对于莫言而言,“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我成长”。此种伴随终生的“饥饿”记忆,在莫言的散文中化为一篇篇表面沉静随性、内里伤痛弥漫的文字记录,以其不夸饰、不矫情的叙述语言,为当今读者描画着曾经的社会历史实相。
在《草木鱼虫》《吃事三篇》《过去的年》《酒后絮语》《也许是因为当过“财神爷”》等关于故乡的篇章中,“饥饿”记忆时时显现于行文之间,成为贯穿始终的核心体验。在与生俱来的饥饿中挣扎长大的孩子,于莫言笔下永远是同一形象,“挺着一个水罐般的大肚子,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在里面蠢蠢欲动”,而且“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在饥饿折磨与生命本能的驱使下,这些孩子都成了“觅食的精灵”,“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百草”包括草根、草籽、野菜、茅草饼、地瓜蔓、干结的青苔、秸秆上的菌瘤、水中的浮萍、房檐上的草、各种树的皮……“百虫”更是名副其实,当地能见到的各种蚂蚱、豆虫、蝈蝈、蟋蟀、蝉乃至金龟子等,都成了孩子们费力搜捕的“美味佳肴”;至于河沟里的鱼、螃蟹、土泥鳅更是特定季节里的必捉食物,癞蛤蟆肉也被传为是鲜过羊肉的至上美味。以故乡生活为叙写对象的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可谓难计其数,但如莫言般将故乡生活的细节以如此本真面貌反复呈现于笔端的,似乎为数甚少。不同于多数作家隔着“八千里路云和月”对于故乡的回顾,无论心理影像抑或笔端描画,都会产生时空岁月过滤后的记忆偏差与情感偏向,也没有一般作家对故乡的理想化观照、俯察式批判或主观化偏爱,莫言始终深深植根于北方乡村贫瘠的土地,特别是在散文写作中,他甚至是有意而固执地将自己重新深置于故土,以持守、平齐、对等的视角,以在场的姿态和方式,一遍遍客观冷静地细察着这方熟悉的地域及其上的人事,并以直露质朴的叙述语言将其合盘托出。
“饥饿”对于生命个体最重的戕害,是对人性尊严的彻底摧残与剥夺。对于一个整日饥肠辘辘的孩子而言,攫取食物成为其最发达的本能。在散文中,莫言毫不隐讳地写了自己年少时为了饱腹而四处偷取食物的“事迹”:抓店家案子上卖的熟猪肉,差点被刀砍掉手指;偷扒刚种下的花生种,因拌了剧毒差点丧命;偷吃生产队的马料,脑袋被按到沤料缸里差点呛死……可是“只要一见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没有道德,没有良心,没有廉耻,真是连条狗都不如”。凡此种种独特真实的情节与直露剖白的心迹,是作家关于故乡最深藏的记忆,却于散文中毫无讳饰地直笔写来,裹挟着一种特别的情感蛮力。关于散文的真实性问题,莫言曾有过多维度的认知与表述。在其散文集《会唱歌的墙》自序中,作家曾坦言:“一个人写小说总是要装模作样或装神弄鬼,读者不大容易从小说看到作者的真面目,但这种或者叫散文或者叫随笔的鸡零狗碎的小文章,作者写时往往忘记掩饰,所以更容易暴露了作者的真面目。”此言可视为莫言散文创作的由衷感言与切实体会,至少在他的故乡题材散文中,我们看到的是鲜活生动的生活细节、真实可感的乡村场景,这些原生态的童年记忆,以激切到有些粗率村野的语言呈现出来,其实是莫言生命深处的浓烈体验与沉郁情绪长期酝酿之后的一种自然宣泄。
莫言在散文中写过饥饿至极的乡亲们挖“白色的土”来吃,这在那个饥荒年代也许不算什么稀奇事;写过乡邻曾传说,有人将饿死的亲人的肉切下来吃,大概也不完全是主观臆想;但其所记述的“吃煤”事件,却无论如何均显得有些奇异:学生们拿学校取暖的煤来吃,且觉越嚼越香,上课时,老师被学生咯咯嘣嘣的咀嚼声吸引,竟然也惊叹其好吃。“这事儿有点魔幻,我现在也觉得不像真事,但毫无疑问是真事”,莫言在《吃事三篇》中写到,“王大爷说,这事千真万确的,怎么能假呢?你们的屎拍打拍打就是煤饼,放在炉子里呼呼地着呢”。莫言关于故乡生活的回忆,在粗粝的质感之上呈示着生活的本真模样,而这些所谓赤裸的现实,有时比“魔幻”显得更为奇异、虚幻、变形、夸张——吃豆饼喝水把胃涨破而死,五六岁的孩子一次能喝下去八大粗瓷碗野菜粥,扑抢麻风病人剩下的半碗面条……凡此种种超乎常人的想象之事,却无比真实地存档于并不久远的历史之中。而母亲常常提起的一个梦境,给少年的莫言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梦中,死去的外祖父在坟墓里亦吃东西,“吃棉衣和棉被里的棉絮。吃进去,拉出来;洗一洗,再吃进去;拉出来,再洗一洗……”令读者更为惊心的,是“母亲狐疑地问我们:也许棉絮真地能吃?”操劳一家衣食的母亲,在贫穷至极、饥饿难耐的日子里,能多发现一种食物的渴望强烈至如此程度!在此种历史情境中,原本听来极其荒诞无稽的梦境,却彰示着真切的本质况味与浓重的象征意味,莫言只须打开心门,直笔写出,便天然具有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效果。这也就难怪莫言一接触马尔克斯的小说便产生了强烈的亲和感,并将故乡故事如此自得地以“魔幻”笔法进行恣意描写。
如果说“饥饿”体验代表的是物质的匮乏与感官的痛苦,那么对于年少的莫言而言,亲情的疏离与淡漠、人世争斗造成的隔膜与伤害、少年辍学离群放羊的孤单与寂寞……带来的是深层心理慰藉与情感满足的严重缺失。关爱的匮乏、温情的丧失、心灵的孤独、尊严的戕害,是莫言“故乡意象”的另一深层内核,也是持续贯通于其散文中的情感倾向。在《超越故乡》中,莫言详细描述了自己因饥饿去地里偷萝卜,被抓住扭送到工地后,领导集合起二百多人,让他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检讨自己“罪该万死”,而在他忐忑不安地回家后,又被父亲用蘸着盐水的绳子暴打了一顿。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而在《漫谈当代文学》等篇章中,则记述了自己“因言获罪”的故事:因为说了几句学校和老师的“坏话”,而被同学告密,“老师大怒,在班里组织了一个严肃的批判大会,让每个同学发言批判我”,一个平日里喜欢的女同学因发不出言,“竟上前扇了我一耳光”,后又被老师用腰带拴在教室后面的床脚上,用弹弓当活靶打……此种人为的伤害与屈辱,来自于年少时的乡亲、亲人、同学和老师,对于敏感自尊的少年的残酷性与深层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至于洪水中一个人生病在家的恐惧与孤独,被迫辍学独自放羊的无奈与寂寞,更是极大地影响并改变了一个少年人的性格。“不幸福的童年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一颗被扭曲的心灵、畸形的感觉、病态的个性,导致无数千奇百怪的梦境和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惊世骇俗的看法。”读懂了这些,也就能更好地理解莫言“故乡意象”的内蕴特质及其整个文学创作中社会认知与历史批判的内在视点和情感根源,甚至其艺术传达的方式。
二、艺术传达:苦难底色中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想象
综观莫言的散文创作,极度匮乏的“饮食”作为贫困、粗糙与严酷的生活的代表意象,是一种生存状况与生命体验的高度浓缩与典型象征。因为“食”者,既关乎生命的本能、官感,亦关乎人生的状态、情感,更关乎人性的内在深层体验。莫言散文中,在吃的方面各种令人羞愧的表现在其回忆中比比皆是:“回想三十多年来吃的经历,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有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子,找点可吃的东西,填这个无底洞。为了吃我浪费了太多的智慧。”因为对于普通人而言,“所谓自尊、面子,都是吃饱了之后的事情”。这种为满足生命本能需求所做出的种种有辱尊严的行为,也许是一些作家刻意回避、淡化甚或美化的,但莫言却于不动声色之中将生命的痛苦挣扎、生存的残酷真相、生活的无奈承受都以其固有的原生态呈示给读者。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与身心感知所积淀下来的人生经验,奠定了其看待社会世态的目光与视角,铸就了其特有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关于童年记忆与故乡印象对于写作者创作的深刻影响,向来论者颇多,而对于莫言而言,双重匮乏的童年记忆成为伴其成长的无法褪去的心理胎记与精神负载,并因为现实生活的深长折磨而累加着无数伤痛,逐渐蔓延为其文学作品的苦难底色。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莫言甚至将“饥饿与孤独”概括为自己创作的财富,视其为创作的原动力与写作的基本内容。因而莫言的创作,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均是对现实冲突与历史苦难的省察与表现。从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到后来的《丰乳肥臀》《檀香刑》《蛙》《生死疲劳》等,自然的灾荒、人世的灾难,具化为饥馑频仍、饿殍遍野、战争动乱、厮杀争斗、人性残酷……历史与现实的重重苦难构成其创作的一贯题材,而对于苦难毫不讳饰甚至有意强化的倾泻式的反复渲染,铺垫为其文学创作的基本情感基调。
《超越故乡》是理解莫言人生经历与文学创作至为重要与关键的一篇散文,作家系统而具体地谈到了故乡经历,包括故乡的人物、故乡的风景、故乡的传说对于自己创作的深远影响。以其为切入点,可以更为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莫言文学创作的源泉与根基。自始至终,“故乡意象”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呈不同姿态,反复被纳入其写作视野、取材范围与表现范畴,化为其文学表现的内容,在各部作品中被反复倾诉,甚至固化成其文学世界的深重内核,构成了其绝大多数作品的“故乡”特质。其最直接的表现,便是对于“故乡意象”的迁移、化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复合、重构与升发。
此处所谓“迁移”,是指作者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情感体验较为直接地移植于文学创作中。莫言自言:“我的小说中,直接利用了故乡经历的,是短篇小说《枯河》和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正是在多篇散文中写到的童年因饥饿偷食物被打受辱的经历,在作家的内心积存发酵,化为真切鲜活的文学创作素材。《透明的红萝卜》中,金色透明状的萝卜、匍匐怪兽般的火车、燃烧火苗样的头巾……写得鲜活灵动,令人赞叹,而这些为人称道的所谓的“童年视角”“神奇意象”“奇妙通感”……实际源于一个曾经饥饿孤独的孩子的内在痛苦及其造成的“真实”幻觉。正如作者所说,“并非只有挨过毒打才能写出小说,但如果没有这段故乡经历,我绝写不出《枯河》。同样,也写不出我的成名之作《透明的红萝卜》”。“任何一个作家——真正的作家——都必然要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编织故事,而情感的经历比身体的经历更为重要。”生活的冷酷真相、情感的冷寂状态,因其是作家的亲身经历与体验,因而诉诸艺术表现时,无论是日常细节还是场景氛围,都呈现着切实可感的本真情态,加之作家独特表达手法与语言的运用,更赋予了作品可触可感、鲜活生动的细腻肌理,因而莫言的“故乡意象”洋溢着现实的“原滋味”,呈示着固有的“原生态”,这也是其文学创作的独特价值所在。正如荣格所言,“原型是领悟(apprehension)的典型模式。每当我们面对普遍一致和反复发生的领悟模式,我们就是在与原型打交道”。作家正是在“原型”的展示中引领读者认知历史真相与内质。
对于生活素材的各种加工,是所有作家巧妙化用经验积累的通用方法。将莫言的散文与小说对照来读,便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作家几十年创作的丰厚文学作品中,典型性的“故乡意象”一直在被反复化用着。《丰乳肥臀》这本以母亲一生事迹贯穿中国现当代历史的长篇巨著,对于母亲平生苦难遭际的描写,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始终伴随着食物匮乏造成的痛苦、无奈、挣扎、妥协甚至生命威胁。“母亲和姐姐们走出村子,在苏醒的田野里挖掘那种白色的草根,洗净捣烂,煮成汤喝。聪明的三姐挖掘田鼠的巢穴,除了能捕到肉味鲜美的田鼠,还能挖出它们储存的粮食。姐姐们还用麻绳编织了渔网,从水塘里捞上苦熬了一冬变得又黑又瘦的鱼虾。”大量诸如此类纤毫毕现而又真切传神的描写,基于莫言已经内化的生活经验,在其散文研读中我们已屡见不鲜。但在长期写作过程中形成的自觉意识又促使作家对熟悉的“故乡经验”不断进行开掘,因而这些早年“刻在骨头上”的记忆,又会以各种不同的“形象”化入其写作过程,极大地丰富了“故乡意象”。仅以自成“序列”的人物形象为例,除了《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儿”,“即使仅从饥饿的角度来看,这些‘变身’也可以列举《铁孩》中吃铁的‘铁孩’和‘我’;《丰乳肥臀》中疯狂恋乳、无法长大的上官金童;《牛》中贪吃好说的罗汉;《四十一炮》中吃成肉神的罗小通……经过多年的累积,莫言笔下的黑孩们已经形成一种特有的形象序列:他们是一群拥有共同精神内核的孩童,同时又是具有同类主题指向的人物,他们每一次出场都体现了莫言在创作上的‘变与不变’”。其根本之“变化”,在于作品传达的不再是个体经验,而是衣食贫乏造成的痛苦表象下深层的生命困顿与普遍性的时代悲剧。
从实际经验到文学创作,是作者不断调动、整合、重构过往经验的一种复杂的能动过程,因而相同或相似的人生经历与情感经验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常常表现得千差万别。即使在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中也会呈现出巨大差异,因为“随着一个作家的经验的不断丰富和变化,他就可能不断地‘修改’他的童年经验,从而变异出新的内容,发现它的新的意义”。因而莫言将其不断拓展的生活阅历、合理丰富的艺术想象,纳入到“故乡意象”之中,从而在复合与重构中凸显“故乡”所蕴含的独特内质及其丰厚意旨。《也许是因为当过“财神爷”》是莫言故乡散文中难得的温情叙事之作。回乡探亲的莫言偶遇昔日的小伙伴,想起二十年前的大年夜,两人在冰天雪地中跑到邻村,扮成“财神爷”讨要饺子的往事。而莫言将其作为生活原型写入小说《白狗秋千架》时,对其形象进行了诸多“重塑”。作家将女性人生中的天灾人祸加诸其身:美丽容貌被毁,丈夫残疾暴戾,孩子先天聋哑,生活劳累贫苦……从美丽热情的少女演变成粗俗可怜的农妇,从“个别形象”叠合成农村女性的共同影像,从而完成了对于一个时代女性集体命运的表达,赋予了人物特出的典型意义。莫言以故乡为出发点与根据地,在文学世界不断开掘,故乡经验及其生成的“意象”在作者持续的历练、增长的见识、丰富的想象、理性的思考的共同作用下,日益累加丰厚,从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理性故乡”。
但优秀作家的超拔之处更在于其对于生活细节和具体物象的艺术升发,他们甚至可以看到并表达出:吃食形象同肉体形象、生产力形象(肥沃的土地、生长、发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莫言在其创作中自觉地在感性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着连类旁触的文化想象:《红高粱》中原始蛮力与“种”的退化的喻示,《酒国》中酒之文化与世象透视的连接,《丰乳肥臀》中“恋乳症”与“侏儒”型人格的象征,《檀香刑》中“酷刑”历史与残忍“看客”心理的揭示,《生死疲劳》中世道轮回与历史悲剧的重演,《蛙》中传统伦理观念与生育“政策”乃至“政治”的胶着……从个体体验推及为群体经验,从童年经历跨越到历史演进,从“地域性”故乡拓展为“普世性”乡土,从“喧嚣式”的外部视察深入到“情感化”的内在体察与“理性化”的深层省察——此种文化想象是对历史记忆与现实经验的升发与创造性的复合,不仅为其作品带来了丰厚的艺术表现内容,亦影响着其文学创作的艺术观念乃至传达形式,辐射出巨大的感染力与冲击力。
三、文学创作:反思中的“超越”与“限制”
所谓的“故乡意象”,对莫言而言,“更多的是一个回忆往昔的梦境……作家正像无数的传说者一样,为了吸引读者,不断地为他梦中的故乡添枝加叶——这种将故乡梦幻化、将故乡情感化的企图里,便萌动了超越故乡的希望和超越故乡的可能性”。此言道出了莫言超越故乡的创作愿望与实践路径。
莫言创作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于“故乡经验”的处理,首先是从心理情感的深处与之进行着根深蒂固的联结,因为“饥饿”与“匮乏”所刻下的永难磨蚀的痛苦经验,规制着他艺术传达的内在视点与情感基调,因而其笔下的“故乡意象”,永远呈现着本真的“赤裸”样貌,即使丑陋、残酷、不堪至不忍卒睹,也绝不回避讳饰,更遑论温情美化,他总是固执地呈现着其外在至本质的全方位真实影像,甚至逼近到触其温湿、探其肌理的距离,不留任何回旋的余地。而其无限放大的“故乡意象”中充盈着的是浓重而恣肆的情感洪流,甚至常呈现出情溢于物、意重于象的表达倾向与审美特征。如果说“从整体上看,当代中国故乡意象的文学建构至少包含两个向度的内容:实体性的故乡与情感性的故乡”,那么于莫言而言,其“故乡意象”的传达更偏重于后者。
莫言的散文与其说是对于自己人生经历的回忆与记录,莫如说是对于自己情感体验与心灵历程的倾诉,这一特征也直接显现于其小说创作中。《卖白菜》当属其最具艺术感染力的散文之一。这篇平直朴实至几乎摒弃了所有结构技巧的短文,讲述了一次母子俩卖白菜的过程,读来却回味深长。作者将与母亲相处的全部体验与深切情感凝聚贯注在看似平铺直叙的行文间,但因其情感底色是“莫言式”的,素朴真率间夹杂着冷峻粗粝的母爱,反而赋予这位平凡普通的母亲形象撼动人心的独特魅力。十六岁出嫁,“从此就开始了漫漫的苦难历程”的母亲,一生可谓饱受折磨,单是各种病痛,在《从照相说起》这篇短文中便写得触目惊心:春天“心口痛”,夏天“头痛,脸赤红”,“翻肠绞胃地吐”,秋天好不容易熬过“心口痛”,冬天又开始遭受哮喘的折磨,脱肛、腰上碗口大的毒疮、带状疱疹……可不管如何疼痛煎熬,也必须硬挺着操劳不息。卖白菜的过程中,面对莫言不舍的泪水,她会掀起衣襟给他擦,衣襟上是“揉烂了的白菜叶子的气味”,“用粗糙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面对莫言的哭闹,她也会“猛地把我从她胸前推开,声音昂扬起来,眼睛里闪烁着恼怒的光芒”,会“声音凛冽”地训斥可怜的儿子……一向坚强的母亲,却因为莫言多算了别人一毛钱而觉得丢了脸,流下眼泪——这样一位普通而又独特的母亲,被艰难生活磨去了温柔细腻,夺走了健康快乐,却坚守着人世最珍贵的道德与品格——这是典型的“莫言式的母亲”:她是莫言贫穷、孤寂生活中唯一的依靠与温暖,但她也会常常半怨叹半忧心地数落儿子;她将被生活剥蚀之后仅余下的温情与怜惜,全部给了莫言,“有时咽到嘴里也得吐出来给我吃”,但也会时常露出苦难赋予的粗糙、严厉、冷冽……因而此类“匮乏”温柔和煦“母性”的“母亲”形象,常以不同的相貌、身份、境遇,反复出现在莫言的诸多作品中,升华成为莫言文学世界女性形象的内核与魂灵。扉页上写着“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的《丰乳肥臀》,被目为莫言的长篇代表作之一,其中的母亲形象正是莫言在“故乡”经验基础上,综合了很多相类的“母亲”的故事而进行的合乎情理的塑造。在莫言的文学王国中,塑造最为成功的,当属一个又一个鲜活丰满、姿态纷呈的女性形象,但无论怎样变化,综观莫言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母亲”的形影隐现于其言行品性间。从《红高粱》中的“我奶奶九儿”,到《檀香刑》中的“眉娘”,从《红树林》里的林岚、陈珍珠,到《生死疲劳》中的庞春苗……她们缺乏传统文化形态中女人贯有的温良贤淑、娇柔文秀,而充盈着散文中所描述的“母亲”的独特性情——泼辣大方、勇于担当、爱憎分明、坚韧顽强……面对生活的磨难与剥蚀,愈发显现出其活泼的生命力与特立独行的姿态,洋溢着一种野性的美。因其倾注了作者对于“母亲”的最深沉的情感,以及对于历史文化中女性意识的深层体悟与反拨式思考,而成为当代文学中的独特“类型性”形象。
而且随着创作的不断进行,走出故乡的莫言反观故乡时,亦在不断地对“故乡意象”及其蕴含进行审视与反思。人生苦难的根源与本质、现代历史的更迭变迁、历史风云中的个体命运、社会问题的追询考问……都被纳入了莫言的创作视野,极大地拓展了其作品的表现范畴。因而,当个人的痛苦体验推及为对于人类苦难的解读、对于生命本体存在意义的深入思考时,当个人的现实经验延展为对于文明历史的探寻、对于社会政治文化的广泛考量时,作家的创作视域与作品的深广维度便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而为了适应如此繁复的内容表达,莫言在创作手法上也在不断进行着探索——借鉴西方现代文学表现手法,回归传统古典文学写作技巧,到多种表现形式综合运用与创造,莫言的文学超越一直没有停止。
《会唱歌的墙》可视为呈现“故乡意象”的一篇美文,故乡的独特风物在莫言沉静而深情的笔下与诗意、哲思乃至奇幻想象和谐交融。而其中心意象“会唱歌的墙”,则是九十九岁的门老头特意修建的,它是“由几十万只酒瓶子砌成的,瓶口一律向着北。只要是刮起北风,几十万只酒瓶子就会发出声音各异的呼啸,这些声音汇合在一起,便成了亘古未有的音乐”。此种描写让人联想起庄子所铺排描绘的天籁之声,但那是风穿过天然孔穴所发出的鸣响,是纯粹自然的乐音与吟咏,而这堵突兀立起的墙,却是用现代社会的大量废品堆砌而成——虽然莫言用特有的繁复倾泻式的语句赞叹其发出的“变幻莫测、五彩缤纷、五味杂陈的声音”,但朴实封闭的小村庄中这堵喧嚣的墙与传统的“故乡意象”似乎格格不入,散发着现代化进程带给乡村的冲突感与诡异感,从而呈现出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故乡意象”——这是走出故乡却又不断回望、离开故乡却又永远汲取的作家心中所创造的永恒而又变幻的故乡意象,并因作家“在思想和形式密切融汇中按下自己的个性和精神独特性的印记”,而凸显出鲜明而独特的莫言式艺术风格。
然而对莫言散文与小说文本序列进行综合性考察,亦可见出,莫言的文学创作在趋向成熟稳定的写作技巧与风格之外,日渐显露出的局促与限度,“故乡意象”在被反复书写中亦日渐表现出对创作的束缚与制约,有时相同的题材会在不同的作品中呈同质化地反复出现。且因为对于故乡之种种过于熟稔,所以作者的观察视角及认知判断容易固化,对于相关人与事的表现有时呈模式化倾向。此外,表层叙事的喧嚣与繁复,有时反而稀释冲淡了内容的表达,难以真正触及历史的真相、社会的本质与人性的微妙。因为“作家当然可以借助调查、采访、阅读等技术手段来弥补个人经历之不足,但这些工作无法改变一个作家被乡土传统、乡土人情制约着的道德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任何一位在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家都应具备这两种特性——突出地表现出来的地方色彩和作品的自在的普遍意义。”英国著名作家托·斯·艾略特此言道出了作家创作应追求的文学审美境界,而“自在的普遍意义”的追寻,也是莫言与当代作家应该不断突破限制、实现超越的努力方向。
◎原文刊发于《求是学刊》年第3期。为了阅读方便,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
◎本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uimuasm.com/ssfz/5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