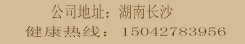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繁衍 > 你好,文学魔幻现实的莫言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繁衍 > 你好,文学魔幻现实的莫言

![]()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繁衍 > 你好,文学魔幻现实的莫言
当前位置: 水母 > 水母的繁衍 > 你好,文学魔幻现实的莫言
莫言
(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男,原名管谟业,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从年开始发表作品《春夜雨霏霏》,年因《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年莫言凭借小说《蛙》荣获茅盾文学奖。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的作品至少已经被翻译成40种语言。
1
书评:
中国现当代读得不多,这本是我看的第一本莫言的小说,张艺谋的同名电影也没看过,所以也从未剧透,这是我看这部小说的背景。
首先,叙述视角给我的感觉最为奇特,这不是褒也不是贬,很明显,叙述人在故事情节中占有一个角色,但是大部分叙述却是全知视角。这点比较奇怪,连狗的视角都有。那场红狗、绿狗、大黑狗的吃尸大战中的狗视角描写,我想只能用“魔幻现实主义”来解释了。至于其他的人物视角描写,似乎全知视角和“我”的人物视角混同,大部分时候“我”都是一个类似“上帝”的存在,能洞察每个人物内心的一切细微情感,也能看到外界一切的风吹草动和大千世界的景观景象。但是很多时候,又突然转回到“我”的视角上来,即作为爷爷奶奶父亲的后代的那个人的视角上。这个“我”时不时地抖抖洒洒地发上一通议论,或者预告一下后面的情节进展和每个人的下场。乍看上去,这个“我”似乎在洋洋得意地挑衅着读者,自己是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都一清二楚的。有时看上去,这种“预告”似乎算是埋个伏笔,作者等到后面再来细细地补充,关于这一点,我放到后面情节那块再说。与视角相关的,是人称方面的问题,因为叙述视角的人物角色,对主人公的称呼——父亲、奶奶、爷爷——一开始看老让我出戏,总感觉人物应该是与这些称呼相对的年龄才对,而不是再往回拨上半个世纪。当然看惯了也就熟悉了。因为人称的原因,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似乎作者至少要写三代人的故事——奶奶爷爷一辈、父亲母亲一辈、“我”这一辈,并且照前面的小说行进速度看,我觉得至少得写个页才能把三代的故事都包括进去,但是我看的这个版本只有三百页多,所以仅从页数上看,似乎后面的虎头蛇尾也是不可避免的了。其次,情节方面,莫言基本上还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插叙也大致如此,这是情节线索的安排问题。粗看前几章,感觉莫言好像不会区分详写略写似的,所有场景,全都细细地进行了描绘,当然由于莫言高超的描写手法,大部分时候并没有流水账之感,但是有的时候,松弛处也确实显得松弛,节奏感似乎一下子断了。总的说来,整部书,主要是前四章,几乎每一处场景以及情节发展,莫言都进行了一种类似还原式的全方位写法,这种详尽并且纤毫毕现的描写手法有其优点,但是缺点也很明显。优点是场景非常具体生动,那些高粱地里发生的战斗似乎如在目前,鲜活异常,声、光、色,尤其是味,全身的感官和情绪都调动了起来,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莫言大场面把握总体感之好,确实令人叹服。包括其他的一些细处场景也是如此,比如爷爷跟恋儿偷情那块,估计莫言写着写着就忘了自己在书中也算一个人物了吧?全知上帝视角大开,画面感极强,或者说是一种类似电影的夸张画面感,所以我想张艺谋把这篇小说改编成电影来拍,应该也不费什么太大的劲的。再来说说缺点吧。缺点就是,把文章按时间顺序来排列的话,几乎就是流水账式的写法了。前几章,几乎没有详略之分,连贯着看下来,尤其是某些暴力恐怖场景,实在是过度骇人,说句笑话,大概算是少儿不宜。可以说,过度的暴力恐怖的渲染令人“叹为观止”。这在我看来,算是个重大缺点。光罗汉大爷被剥人皮那块,先是作者反复预告要剥人皮啦,剥人皮啦,我以为就这么略过去了,按常理,大概也是不会再详写了,谁知后面仔仔细细,一丝不落地全写了出来!莫言似乎也很享受写这些恐怖至极的场景,而且看下去,后面类似的场景也比较多,真是毛骨悚然。诺曼?梅勒说留给20世纪后半期的文学冒险家们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只有性了,连带着大江也连连赞同(至少在他的儿子出生前是如此),我想莫言大概会笑笑,因为梅勒不知道在中国,还有这些原始而又乡土的可怖场面可写。总得说来,我认为恐怖场景和性描写,都可以适当写一写,但是过度渲染的话,似乎有损于艺术美感。至于情节上,还有个颇大的硬伤,那就是前面提到的虎头蛇尾。前几章大场面描写,虽然无详略分野,但起码主线明确,就是围绕着爷爷父亲这两个男主人公以及女主角奶奶写的。但是到了最后一章,不知怎的,引入了些新人物,颇有些蛇尾之感,看出来莫言想写写年后的高密东北乡,但是不知是惧怕着什么,莫言没有交代余占鳌是怎么到了日本北海道的,也没有交代父亲是怎么后来变成了杀人如麻的铮铮汉子的,更没有交代刘氏、倩儿是怎么回到父亲和爷爷身边的,甚至前面埋了伏笔的柳框里的可怕魔王小孩,到了最后一章也没露个正脸,只是在别人的只言片语里略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恶行,但是形象仍然异常单薄,远远比不上前几章里塑造的一些次要人物鲜明。可能作者有些难言之隐,我也不好过多推测,毕竟“解放后”的社会,要是再说某些人的坏话,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吧。再来说说语言方面。汉译小说相对而言,我看的最多,可以说口味几乎就是被那些翻译家们模造出来的,讲究用词的准确,不含糊,A选项比B选项好,那就一定要选A,而不是选择B,甚至C或者D。但是看看莫言这部小说里的语言,似乎作家并不怎么喜欢精雕细琢,这点其实也很明显,有些地方,作家信笔由缰了去,四字词语乱蹦乱跳,挑出来看或许就是个病句或者病词,但是放在整体里来,有时却也无大碍,而且也比较符合全书营造出的浓烈乡土气息,使得感情表达非常浓厚等等。最后再来说说结尾部分,其实又绕回到了情节问题上来了。二奶奶坟头显灵,很明显,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但是有点抄袭教科书之感,相比起前几章来,实在是生硬得很。而且最后“我”站在坟头里作的那些类似于“全文总结式”的感慨,这更是作文式的程式化结尾了!总之,在我看来,这个结尾算是一大败笔。不管怎么说,瑕不掩瑜,有空再看看莫言其他的小说吧。(感觉我这结尾似乎也落入了程式化结尾的圈套了?)
精彩片段:
人血和人肉,使所有的狗都改变了面貌,它们毛发灿灿,条状的腱子肉把皮肤绷得紧紧的,它们肌肉里血红蛋白含量大大提高,性情都变得凶猛、嗜杀、好斗;回想起当初被人类奴役时,靠吃锅巴刷锅水度日的凄惨生活,它们都感到耻辱。向人类进攻,已经形成了狗群中的一个集体潜意识。父亲他们的频频射杀,更增强了狗群中的仇人情绪。
由于吞吃人肉,所有的狗的白眼球上都布满密密的血丝,几个月吞腥啖膻、腾挪闪跳的生活,唤醒了它们灵魂深处的被千万年的驯顺生活麻醉掉的记忆。现在它们都对人——这种直立行走的动物——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在吞吃他们的肉体时,它们不仅仅是满足着辘辘的饥肠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它们是在向人的世界挑战。是对奴役了它们漫长岁月的统治者进行疯狂报复。
奶奶最先吸引了单廷秀目光的这双小脚,奶奶最先唤起了轿夫余占鳌心中情欲的也是这双小脚。奶奶为自己的脚自豪。只要有一双小脚,即便满脸麻子也不愁嫁;只要有一双大脚,哪怕你脸如天仙也没人要。奶奶脚小脸俊,是当时的美女典范。——我觉得,在极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女人的脚,异化成一种准性器官,娇小玲珑的尖脚使那时的男子获得一种包含着很多情欲成份的审美快感。
1
2
书评:
schatz
现在才看到这本书,总算看到有人写出来这个疼痛的伤口。这个黑暗中的伤口一直默默散发出无法愈合的脓血味,困扰我多年。如今阳光总算照进来。我可以放下它了么。我知道在这个国家的种种虚幻表象下,藏着对人类生命核心的一种持续的撕裂。起初只是发现冰山一角,听闻有老人在立交桥下捡到一个肋骨下插着剪刀的带血的弃婴。我循着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的踪迹前往,不知不觉踏进了无边的血池地狱。我无法忘记上了年纪的妇产科医生在饭桌上讲述当年把酒精注入正在啼哭的婴儿头颅。无法忘记送走了孩子的年轻女孩在寒冷空旷的马路上撕心裂肺哭泣。无法忘记被杀死之前的孩子B超照片里像天使翅膀一般挥舞的一双小手。民政部官员冷漠的脸,无解的难题如同不见底的黑暗深渊。这个民族刚刚进行过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自己切断了自己的生命之源。它的凋零已经止不住了。我只是有幸得赎自己的原罪,得以洗刷自己出生之前埋藏的悲哀。我只觉得感恩。我可以自由了么。ValueRunner写东西可能就和唱歌一样。越经历练,就越远离热闹,走向含蓄。脑子里转了很多个圈,但只写下几行字。不再追求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而是写下最简练的句子,渗入自己的情感和想法。莫言讲故事的本事和语言的魅力毋庸置疑。原来买过本莫言小说集,讲土匪的爷爷奶奶(好像叫黑色闪电还是什么),又读到他的一篇《枯河》,顿时觉得这人很牛,写文字动用五官,很震撼。但所谓酝酿几载几易其稿的这部作品读起来却是那么不给力。不够乡村也不够魔幻。不够深情也不够辛辣。脑海里面想了很多圈但其实写下来的却有点拖沓,太平淡,不知所云。后面写到当下的社会,更是一塌糊涂,一点都不靠谱。真是部写崩了作品,也就是翻译起来方便一点。老非完全失望了;没有《红高梁》里血的恢弘和深刻;没有《食草家族》里魔幻、《天堂蒜薹之歌》里的疼痛、《丰乳肥臀》里的苦难、《生死疲劳》里的诡异。貌似高举着直入现实的深处荣光大旗;胶东半岛和它上面发生的生生死死显得如此的敷衍和苍白。没有深入那具有力量、光仪式感、巨大悲剧意识的在血水中的挣扎和飞翔。诞生是伟大的。而莫言先生的笔触是如此的无力和渺小。仲秋月含颦以“蛙”来折射“娃”的问题,写好了叫妙笔生花,写不好就成了牵强附会,莫言这本书成了今年茅盾文学奖的赢家,是因为它反映了计划生育这个历史问题,然而我觉得小说的后半部分没有前半部分那样真实,反而更加虚飘,虽然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荒唐的,我也见识了不少人情冷暖,然而可能是内心对于男女、情理和正邪的权衡,使我对后半部分的故事愈发的感到无力,感到无望。蝌蚪、姑姑和小狮子这三个主人翁,说好了是在不断忏悔中苟且,说白了就是一帮自欺欺人、事后诸葛亮的虚伪屠夫。陈眉的痛苦、女人的无奈,命运的多舛,我们只能望而叹之,却无能去定夺,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吃人的后代,自己也吃着人……我向来是不吃青蛙的,原因复杂;然而那些历史的替罪羊们,他们即便供着青蛙烧香拜佛,内心确是得不到片刻安宁的。女娲造人出淤泥不染,而我们自己却满身血泪。从蛙到娃,我们进化抑或退步了?海山·野火生儿子的魔咒给农村妇女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痛苦。书里有句话触目惊心:孩子被拉出产道之后,母亲就像到空了粮食的干瘪口袋。一个女人能被倒空几次呢有人说了,女人生孩子天经地义,就像土地要长庄稼。但他们从不想想庄稼种多了土壤也会贫瘠,对他们那多产的老婆也不会心存感激,反而要揍上一顿,咒骂着这只蠢母鸡生了一堆赔钱货。不要说什么爱孩子,喜欢孩子,听了我就要发笑每天在田里头拱地的劳累了一天,回到家还要照顾嗷嗷哭喊的一群小崽子,她最渴望的就是休息。
精彩片段:
1、所谓爱情,其实就是一场大病。我的病就要好了。2、钱不花就是一张纸,花了才是钱。3、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利去死,他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4、但那是历史,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许多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5、想起母亲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痛苦,一个女人不生孩子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女人,而且,女人不生孩子,心就变硬了,女人不生孩子,老得格外快。6、生育繁衍,多么庄严又多么世俗,多么严肃又多么荒唐。7、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显微镜下。8、这么多年来,我总结了一条经验,解决棘手问题的最上乘方法是:静观其变,顺水推舟。李手说。9、我想起母亲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女人生来是干什么的?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而来。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痛苦,一个女人不生孩子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女人,而且,女人不生孩子,心就变硬了,女人不生孩子,老得格外快。10、一个自认为犯有罪过的人,总要想办法宽慰自己,就像您熟知的鲁迅小说《祝福》中那个捐门槛的祥林嫂,清醒的人,不要点破她的虚妄,给她一点希望,让她能够解脱,让她夜里不做噩梦,让她能够像个无罪感的人一样活下去。我顺从着她们,甚至也努力地去相信她们所相信的,应该是正确的选择吧。尽管我知道那些有科学头脑的人会嘲笑我,那些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人会批评我,甚至会有个别有觉悟的人会向有关方面控告我,但我也不想改变,为了这个孩子,为了姑姑和小狮子这两个从事过特殊工作的女人,我宁愿就这样愚昧下去。11、其实,她说,蛙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人跟蛙是同一祖先。她说:蝌蚪和人的精子形状相当,人的卵子与蛙的卵子也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你看没看过三个月内的婴儿标本?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与变态期的蛙类几乎是一模一样啊。12、恋别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恋自己不需要,我想怎么爱我自己,就怎么爱我自己。13、好哥哥们,你们打死我,我要感谢你们。但你们不要吃青蛙......青蛙是人类的朋友,是不能吃的......青蛙体内有寄生虫......吃青蛙的人会变成白痴......14、在我的印象中,姑姑胆大包天,这世界上似乎没有她怕的人,更没有她怕的事。但我和小狮子却亲眼看到她被一只青蛙吓得口吐白沫、昏厥倒地的情景。15、送姑姑英纳格手表的人,是一个空军飞行员。那个年代的空军飞行员啊!听到这个消息后,哥哥姐姐像青蛙一样哇哇叫,我在地上翻筋斗。16、我端详着这只巨蛙,心生敬畏。只见它脊背又黑,嘴巴碧绿,眼圈金黄,身上布满藻菜般的花纹和凸起的瘤点。那两只突出的大眼睛,视线阴沉,似乎在向我传达着远古的信息。17、你姑姑不是人,是妖魔!岳母跳出来说,这些年来,她糟蹋了多少性命啊?他的双手上沾满了鲜血,他死后要被阎王爷千刀万剐!18、农民们可以流动着生,偷着生,而富人和贪官们也以甘愿被罚款和“包二奶”等方式,公然地、随意地超计划生育,满足他们传宗接代或继承亿万家产的愿望。大概只有那些工资微博的小公务员,依然在遵守着“独生子女”政策,他们一是不敢拿饭碗冒险,二是负担不起在攀比中日益高升的教育费用,即便让他们生二胎也不敢生。
19、只要出了“祸门”,就是一条生命,他必将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合法的公民,并享受这个国家给予儿童的一切福利和权力,如果有麻烦,那是归我们这些让他出世的人来承担的,我们给与他的,除了爱,没有别的。
3
书评:
马世芳(豆瓣)《生死疲劳》是莫言最新的长篇小说,四十五万字的篇幅,即使以莫言的多产健笔,也算得上是近年来野心极大的尝试。莫言自谓为了写这部书,他弃电脑而回归稿纸,使用「一次性的软笔」(或许是咱们所谓的中性笔?),一鼓作气、每天只睡两三小时,连续拼了一个半月便告完工,并谓他重新从「手写」的动作中,得到了莫大的乐趣和成就感。他也不忘强调,这个故事在他心里已经琢磨了几十年,这次只是时机成熟,终于决定一古脑儿把它写下来。
尽管苦了编辑和校对,但想到那厚厚一沓的手稿,诚然令人神往。迭有作家自谓,写长篇小说不仅是对个人精神与生活习性的大挑战,也必须有极好的体力,莫言写《生死疲劳》的过程,或许又可作为一例。这部书据云在年春初版即有十二万册的印量,并且很快再版,尽管和动辄百万册计的畅销书无法相比,一本纯文学的创作,以其厚重篇幅和较高的定价,能有这样的回响,也算是中国作家之中极为难得的「高标」了。这部小说延续了《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的「大河式家族史诗」主题。在叙事技巧上,莫言以堕入「六道轮回」、屡次转生为畜的地主「西门闹」的叙事观点作为第一人称的主轴,从年一路写到年,加上后设式的「蓝解放」与「大头儿」倒叙的对话,再穿插故事中角色「莫言那小子」的叙事角度,来补足第一人称叙事所不能及的观点。这样既能收全知全能之效、得以有效地推进情节,又以真假莫辨的多重视角尽量地避开了全知全能「说了算」的限制,是一套非常精巧复杂的叙事结构,然而读起来并不吃力。莫言自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大陆翻译引进的大批拉丁美洲小说作品,是他极为重要的启蒙经验。综观莫言几部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叙事观点」与「叙事语言」确实一直都是他念兹在兹的重点,对长篇小说「结构工程」的试探,对「形式」与「内容」一体两面的探索、对「史诗」的执迷、寓「国族大叙事」于「家族小历史」的笔法,也让我们似乎窥见了拉美小说大家巴加斯.略萨与马奎斯的影响。早期《红高粱家族》()「我爷爷、我奶奶」的叙事角度让人耳目一新,《天堂蒜薹之歌》()和《檀香刑》()对民间戏曲、民间音乐的融合挪用,更是他在「小说语言」开疆拓土的试验。这次莫言借用「六道轮回」的观念,以畜牲的眼光叙说故事,继《檀香刑》「多人轮流独白」的形式之后,再次找到了全新的「说故事腔口」,确实别出心裁。至于跳跃的多重视角,则是诸前辈小说家搬弄多年的「老哏」,也是莫言在前作反覆展演的招数,也算是玩入化境、举重若轻了。寻找到「正确的」叙事方式、掌握小说的整体结构,确实至关重要,这让莫言得以「顺当地说故事」。但私以为真正重要的,仍然是「语言」和「角色」。莫言的语言仍然酣畅淋漓,无论是白描或人物对话,在在生动无比,是第一流小说家的示范。不免可惜的是,这回他又重蹈了《丰乳肥臀》()的覆辙,到了最后一部,节奏乱了,收尾收得有些潦草,「小说家之声」忙不迭地跑出来,把许多原本可以留著点儿余韵的场景情节添上了注脚和教训,通通讲白了,意思就小了。我们未必会介意莫言的乱跑野马、无休止地岔题、以及许多为炫技而炫技的写作表演。这些喋喋不休、芜蔓庞杂的枝枝节节,其实是阅读莫言作品不可分割的乐趣。然而,《生死疲劳》结构上的头重脚轻、匆促收场,还是不禁让人若有所失。多么希望莫言在最后一百页能坚持前面四百多页的叙事节奏,夹沙带泥地,把那些重要角色纷纷退出舞台的极度戏剧化场面,就像百老汇舞台剧终幕管絃齐鸣的大高潮那样用力交代完,或者换个方式,干脆让这部书在四百八十页以内收尾,或许都比现在这样留著个「兔子尾巴」好些。不过,《生死疲劳》无论如何都还是一部精彩的大书,写得最好的段落,足以催人泪下。比起前作《四十一炮》()的不知伊于胡底,《生死疲劳》回归「章回体」的精神,回过头来「好好从头说一则故事」,无论如何都是可喜的。理智上我明白这部书的结构有著无可回避的缺陷,然而情感上我全心拥戴它,并且感谢它。
在我心目中,莫言「完美的长篇代表作」似乎还没写出来──我是说,像马奎斯《百年孤寂》、巴加斯.略萨《酒吧长谈》、葛拉轼《锡鼓》那样的钜制,在人物、结构、语言各方面的平衡,使它能兼顾雄大的野心与细节的讲究。以莫言的才华和活力,五十岁出头的壮年,他的体内应该藏著不只一部同等级的精彩作品吧,我们很愿意继续等待。
精彩片段:
在集市的中央,也就是供销社饭店前那片空场上,县里的“金猴奋起”红卫兵总司令“大叫驴”小常和西门屯里的“金猴奋起”红卫兵支队司令“二叫驴”金龙会师,二人握手,致革命敬礼,眼睛里都放射红光,心中都荡漾着革命豪情,他们也许联想到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会师,要把红旗插遍亚非拉,把世界上受苦受难的无产阶级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两支红卫兵队伍会师,县里的和村里的。两批走资派会师,驴县长陈光第、驴屌书记范铜、打牛胯骨的阶级异己分子兼走资派洪泰岳、洪泰岳的狗腿子、娶了地主小老婆的黄瞳。他们也偷偷地观望,用眼神传达反动思想。低头低头再低头,红卫兵把他们的头按下去按下去,按到不能再低,屁股翘起不能再高,再一用力,扑通跪在地上,揪着头发抓着脖领子再拎起来。
我举起红缨枪,对准她的胸膛,她挺起胸膛,往前送:戳吧,你有种就戳死我吧!我早就活够了,我活得够够的了。说着,眼泪就从她好看的眼睛里滚了出来。这有点莫名其妙,这有点难以捉摸,这个互助,从小跟我一起长大,小时候我们都光着屁股在沙土堆上玩耍,她突然对我双腿间的小鸡鸡发生了兴趣,回去哭着跟她娘吴秋香要小鸡鸡,为什么解放有我没有,吴秋香站在杏树下大骂:解放你这个小流氓,再敢欺负互助,小心我把你那鸡巴给你剪了去!往事历历在目,但一转眼这互助就变得比河里的鳖湾还要深不可测。我转身逃跑,女人的泪,我受不了。
4
书评:
徐小萌(豆瓣)开头第一句话立即让我又想到了《百年孤独》,仿佛还没从八十年代外国文学引进后借鉴模仿的热潮中走出来,令人感到打不起精神来。但是从第二句话开始,莫言就以充分的自觉和自信,完全进入了一种饱满热烈、浸透着中国乡土气息的叙述腔调,再也看不到任何其他作家的影子。这种有时竟与戏文相仿佛的叙述狂野恣肆,很明显作者本人也相当乐在其中甚至不能自拔,让我不时为自己小说叙述的古板僵硬感到汗颜。
《檀香刑》的功力无疑是炉火纯青的,即便是在别的中国当代作家手里很容易流于形式游戏的多视角交替叙述、打乱时间顺序重组叙述等等手法,也在莫言手里变得圆融而不露痕迹。“先锋文学”的“先锋性”也脱下了实验的外衣,不再以自己为吸引眼球的中心,而是与主体天衣无缝地结合之后悄悄退出了聚光灯的照耀。单以变换多视角叙述来说,《檀香刑》甚至比《我的名字叫红》更为成功和精彩。当然这里很可能有翻译的问题,我可以想象那不同人物的迥异的腔调可以轻易在翻译当中损失殆尽。最简单的例子是人称:孙眉娘、孙丙和小甲自称“俺”,赵甲自称“我”,县太爷自称“余”,英语连三种人称都无法区分(汉语在这一点拥有无与伦比的精确性,将来在别处展开细说),遑论更多的语气和腔调。
但是,当这一系列的异彩纷呈在最后一句话戛然而止之后,小说却好像让人品不出余味,听不到余音。结束就结束了,在看到那么多热闹与惨烈之后,心里其实波澜不惊。结尾莫名其妙的最后一句话,是继开头之后的第二大败笔。不过我想更主要原因是两点:命运和态度。我一直觉得成功的长篇小说要从命运的高度来把握人,《包法利夫人》是如此,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是如此。命运的把握是长篇小说的力量和灵魂所在。在《檀香刑》里面,我们看到了离合、聚散、浮沉、生死,但看来看去,看到的只是情节,而不是命运。四个主要人物(主要人物也太多了):孙眉娘嫁了笨老公然后移情别恋,县太爷钱丁想做好事而不成,孙丙造反而被杀,赵甲当了一辈子刽子手退休了又被叫出来干活——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的,我们没有从中看到命运的细腻的推手,也很难感觉到时代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中间的微妙的化学作用。有情节而无命运,小说的力量就弱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看小说常常会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可是看《檀香刑》,我仿佛是从一个盒子外面事不关己地看着盒子里面的人们东奔西跑,主人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并不牵动我的神经。这背后的成因是作者虽然采取了狂欢式的叙述腔调,却故意把自己的态度隐藏了起来,站在一个客观的不动声色的角度来写这些纷纷扰扰。
余华曾经引用过一个观点:“态度会过时,但事实永远不会过时。”我强烈反对这个说法——且不说按他的说法这个观点本身就会过时。事实发生过之后就消失不见了,但是态度却可以因为它所体现的时代而不朽。从托尔斯泰到卡夫卡,他们并没有提供多少我们闻所未闻的事实,他们的力量恰在于态度——自己的态度,自己对别人的态度的态度。《檀香刑》抽离了态度,也抽离了情感,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段其实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的情节,无论叙述本身多么精彩而宏大,也无法支撑一个缺乏态度和情感投入的作品。相比之下,莫言早期的《红高粱》虽然叙述更为质朴,却更加丰满而充满力量。
精彩片段:
赵甲往前跨一步,与钱雄飞站成对面,徒弟把精钢锻造的凌迟专用小刀递到他的手里,他低沉地呜噜一声:“兄弟,得罪了!”钱雄飞竭力做出视死如归的潇洒模样,但灰白的嘴唇颤抖不止。钱的掩饰不住的恐惧,恢复了赵甲的职业荣耀。他的心在一瞬间又硬如铁石,静如止水了。面对着的活生生的人不见了,执刑柱上只剩下一堆按照老天爷的模具堆积起来的血肉筋骨。他猛拍了钱雄飞的心窝一掌,打得钱双眼翻白。就在这响亮的打击声尚未消失时,他的右手,操着刀子,灵巧地一转,就把一块铜钱般大小的肉,从钱的右胸脯上旋了下来。这一刀恰好旋掉了钱的乳粒,留下的伤口酷似盲人的眼窝。赵甲按照他们行当里不成文的规矩,用刀尖扎住那片肉,高高地举起来,向背后的袁大人和众军官展示。然后又展示给操场上的五千士兵。他的徒弟在一旁高声报数:
“第一刀!”
他感到那片肉在刀尖上颤抖不止,他听到身后的军官们发出紧张地喘息,听到离他很近的袁大人发出不自然的轻咳,不用回头他就知道众军官的脸已经改变了颜色。他还知道,他们的心、包括袁世凯袁大人的心,都跳动得很不均匀,想到此他的心中就充满了幸灾乐祸的快感。近年来,落在了刑部刽子手里的大人们实在是太多了,他见惯了这些得势时耀武扬威的大人们在刑场上的窝囊样子,像钱雄飞这样的能把内心深处对酷刑的恐惧掩饰得基本上难以党察的好汉子,实在是百个里也难挑出一个。于是他感到,起码是在这一刻,自已是至高无上的,我不是我,我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我是大清朝的法律之手!他将手腕一抖,小刀子银光闪烁,那片扎在刀尖上的肉,便如一粒弹丸,嗖地飞起,飞到很高处,然后下落,如一粒沉重的鸟屎,啪唧一声,落在了一个黑脸士兵的头上。那士兵怪叫一声,脑袋上仿佛落上了一块砖头,身体摇晃不止。按照行里的说法,这第一片肉是谢天。一线鲜红的血,从钱胸脯上挖出的凹处,串珠般地跳出来。部分血珠溅落在地,部分血珠沿着刀口的边缘下流,濡红了肌肉发达的钱胸。第二刀从左胸动手,还是那样子干净利落,还是那样子准确无误,一下子就旋掉了左边的乳粒。现在钱的胸脯上,出现了两个铜钱般大小的窟窿,流血,但很少。原因是开刀前那猛然的一掌,把钱的心脏打得已经紧缩起来,这就让血液循环的速度大大地减缓了。这是刑部大堂狱押司多少代刽子手在漫长的执刑过程中,积累摸索出来的经验,可谓屡试不爽。钱的脸还保持着临刑不惧的高贵姿态,但几声细微得只有赵甲才能听到的呻吟,仿佛是从他的耳朵眼里冒了出来。赵甲尽量地不去看钱的脸,他听惯了被宰割的犯人们发出的凄惨号叫,在那样的声音背景下他能够保持着高度的冷静,但遇到了钱雄飞这样能够咬紧牙关不出声的硬汉,耳边的清净,反而让他感到心神不安,仿佛会有什么突然的变故出现。他聚精会神地把这片肉扎在刀尖上,一丝不苟地举起来示众,先大人,后军官,然后是面如土色、形同木偶的士兵。他的助手在一旁高声报数:
“第二刀”
据他自己分析,刽子手向监刑官员和看刑的群众展示从犯人身上脔割下来的东西,这个规矩产生的法律和心理的基础是:一,显示法律的严酷无情和刽子手执行法律的一丝不苟。二,让观刑的群众受到心灵的震撼,从而收束恶念,不去犯罪,这是历朝历代公开执刑并鼓励人们前来观看的原因。三,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无论多么精彩的戏,也比不上凌迟活人精彩,这也是京城大狱里的高级刽子手根本瞧不起那些在宫廷里受宠的戏子们的根本原因。赵甲在向众人展示挑在刀尖上的第二片钱肉时想到了多年前跟随着师傅学艺时的情景。为了练出一手凌迟绝活,狱押司的刽子手与祟文门外的一家大肉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遇到执刑的淡季,师傅就带着他们,到肉铺里义务帮工。他们将不知多少头肥猪,片成了包子馅儿,最后都练出了秤一样淮确的手眼功夫,说割一斤,一刀下来,决不会是十五两。在余姥姥执掌狱押司刽子班帅印时,他们曾经在西四小拐棍胡同开办过一家屠宰连锁店,前店卖肉,后院屠杀,生意一度十分兴隆。但后来不知是什么人透了他们的底儿,使他们的生意一落千丈,人们不但不再来这里买肉,连路过这里时都避避影影,生怕被他们抓进去杀了。
出品:路遥文学社——布谷诗社
编辑:文学社自媒体中心
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uimuasm.com/ssfz/326.html